不写游记了
“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转眼已经是第12届了,今年由浙江大学承办,在安吉百草原举行。
去年在西安的会议我翘了没去,今年我也没有交论文,不过还是来了,承担了两场点评,也算有一些发言。
以往每届会议我大多会发表一篇非常“毒舌”的长篇综述,把所有人的报告挨个批评一通。这个传统大概是从2010年的海拉尔会议开始的。事实上,第一次写综述是应吴老师的要求,我当时说我不会写综述呀,吴老师说,就按你平时写博客的风格写就行了,然后我就写了……写完后发给吴老师看,心想这能派上用场吗,没想到吴老师转手就给群发给所有参会同行了。当时许多其他老师在惊讶于发言辛辣的同时,也都表示鼓励,于是我这个胆大包天的毒舌传统也就延续了下来。
我之所以敢于写“毒舌综述”,不完全是初生牛犊的莽撞。第一,是缘于吴老师和吴门同学的感染,尽管我的所谓犀利在吴门也算是较突出的,但并不异常,我们每周讨论论文时互相争论批评都是直言不讳不留情面的;第二,是亏得其他参会老师的包容,显然吴老师最初立马把我的综述转手群发的举动并不是为了害我,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同行老师是能够宽容对待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近年来,我的“毒舌”程度应该是有所收敛了,虽然说我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但由于措辞比较任性,有些语言显得攻击性较强,现在我有所控制,争取在保持“犀利”的前提下减少“毒”的成分。
从这届起,我干脆就不再写全面开火的综述了,就挑一些印象较深的话题,来选择性地记录一些。所以以后再没有“游记”,一律改为“选评”。
这也不是因为我随着年龄增长,终于变圆滑了之类。事实上我就事论事的胆量和底气丝毫没有削弱。这种调整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变懒了,不解释;第二,参会同行的论文总体水平确实有所提高,有个别没啥提高的人呢,也没必要多批评了;第三,当年与老师们不熟,现在逐渐地很多都比较熟了,这不是说熟了就不好意思批评,而是说很多情况下可以当面直接交流。
下面就选取会上讨论的一些问题略加记述。
一、人工智能的心学
第一篇报告就是张祥龙老师的“人工智能与广义心学”。祥龙大师真的是吾辈楷模,尤为让人敬仰的是他真挚的求学态度。他不只是博览经典文献,对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发展也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从观点学说来说,崇尚“复古”的祥龙大师无疑是保守派,但“复古”的理想丝毫没有闭塞他的视野,可以说他对前沿科技和前沿学术问题的关注和了解甚至要超过大多数年轻学者。
尽管如此,他在面对我们这些年轻学者的时候,仍然是持着一种平等,乃至是求教的态度来交流的。他参加会议的认真态度更让我们这些偷懒的划水的人自惭形秽,非但每次都带文章来讲,也认真参与全程会议,甚至是比较糟糕或者枯燥乏味的论文也认真倾听,并总能够提出温和而中肯的建议。
祥龙大师这次的论文首先讨论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某种非常重要的趋势,那就是AI在某种意义上开始获得了某种“时间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人类心智的基础。如果照此趋势继续发展,未来的人工智能极有可能发展出类似人类的“心”。但如何去塑造这种机器之“心”,并不是必然的事情,祥龙大师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古老的心学传统(包括中国的,更主要是印度的)去试图理解并引导这种尚在萌芽中的“心”。
会上的讨论基本上都集中于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有心这一问题上,对于心学的应用倒是没什么讨论。吴老师和东林师兄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虽然看起来高明,但是基本的逻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仍然是机械的、算术的,究其根本无非还是数据的处理。并不是真的形成了某种时间性的记忆。
关于人工智能,我以前的文章倒是强调它的连续性的,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从石器开始,技术就是某种“人工智能”了。但在这里,我倒是要帮祥龙大师说话了,因为虽然有连续性,但也存在另一尺度上的跳跃性。就好比说进化论给出的图景是连续的,但其间确实又有跳跃或“涌现”。究其根本,人无非是由电子原子构成的,但盯着电子原子看,是永远看不出人之为人的特性的;同样,从单细胞动物到人类,在进化史上也是连续的,但又不能说人的心智和阿米巴虫是一回事。所以我指出吴老师犯了滥用还原论的错误,虽然从底层上看,电脑无非就是“数据处理”而已,再怎么花式数据处理还是数据处理,在数据处理的层面上当然是看不到心智的,就好比在细胞运动的层面也看不到人的心灵。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形成某种自下而上复杂性不断叠乘的涌现结构,让新的性质在更高的层面上涌现出来。
目前的人工智能的记忆或时间化能力当然比不上人,但它比起阿米巴虫如何呢?比起水母海蜇之类的如何呢?如果它已经能够在非常低级的程度上拥有某种意识,而技术的趋势又能够让它把这种特点不断强化升华,那么离它拥有比得上人类的时间化能力,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后来张东林师兄与我讨论的时候还说道,和生物不同,人工智能所谓的涌现,每一步每一层仍然都是数据处理,怎么就能够涌现出智能呢?这个论证有点“乞题”的嫌疑,因为所谓人工智能,就其物质构成而言,就是指的某种“完全由数据构成的系统”,问“人工智能能否有心智”,其实问的就是“一个完全由数据构成的系统能否有心智”,如果你预先就认定了全是数据就一定不行,那么这个问题就无从争论了。人这种生物吃的是肉拉的是屎,但计算机这种东西吃进去的是数据排出来的也是数据,每一部分每一环节都是数据。我们的问题就是这种完全数据化的存在是否可能形成心智,而我们注意到,虽然哪哪都是数据,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技术,改变了原先处理数据的方式,不是把所有数据一视同仁,而是在数据中构建起非常深的层级,最底层的数据输入通过一层一层的处理才最后达成输出,而这里头只有最表层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是程序员能够理解和掌控的,而整个系统的构成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AI自行运作的,而这种运作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时间性,且没有终极的完成状态。
当然了,借助深度学习,电脑所涌现出来的新特征或提示出来的新趋势,究竟是不是指向某种“心智”的诞生,这肯定是有争议的。再怎么相信电脑有心智的人,也很难同意这种心智和人类的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命名这种东西,但无论如何,深度学习肯定是带来了某种新东西,预示了某种新趋势。如果还是以为AlphaGo和深蓝没啥两样,这肯定是短视的。无论再怎么强调数据只是数据、机器只是机器,也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深度学习究竟改变了什么?在AlphaGoZero的从零开始的“学习”过程(哪怕称不上学习,总之是这样一个花费几天时间自我提升的运算过程)之中,涌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区别是显著的,你把“深蓝”搁在那里晾3天,再让他和卡斯帕罗夫对战,它的棋力不会提高,原来五五开3天后还是五五开,原来七三开3天后还是七三开;但是你把AlphaGoZero搁在一边晾上几天,程序员啥都不管就纯粹让它开着,再回来和柯洁打,它的棋力就提高了,原来五五开现在可能十零开了。两台AlphaGoZero放在一起,一台断电一台通电,隔上几天,棋力就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程序员或工程师参与,单纯搁在那里的那几天里,发生的究竟是什么?祥龙大师的解释是: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化”能力,这是正内在心智的特点。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但总得有别的说法。不应该在技术领域确实发生了如此显著的新现象时,装鸵鸟看不见。
事实上我就不太同意张老师的理解,我认为这不是单数的心智,而是复数的繁衍过程。AlphaGo与其说是“一个”心智,不如说是一个生态系统,里面有无数成员不断在裂变和竞争,最后我们在表面上看到的时间性,其实是生态系统“进化”的时间性,而不是个人心智内省和修炼而形成的时间性。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拥有心智的最大障碍在于“身体”,因为身体的缺乏,让电脑,或者说让单纯的数据,难以形成“一”,难以形成“自我与他者”的稳定界限。电脑的硬件边界只是让我们看起来似乎是“一台”,但“对电脑而言”却不是它的边界,因为它究其根本而言只是数据,而数据与数据之间随时都在发生分裂和重组,很难形成稳定的界限。在搁置AlphaGo让它自行运转的时候,它是自己分裂成无数虚拟的棋手自相博弈的,所以本质上没有“一台AlphaGo”,一台AlphaGo同时也就是无数台AlphaGo。一台电脑更像是“一窝蜂”而不是“一个人”。个体之“一”如何在数据和程序之间建立起来,是一个大问题。
二、与分析哲学搏斗
在开幕式上,吴老师提到我们会议每次都要请一些分析哲学领域的学者来参与,因为现象学得“与分析哲学搏斗”。今年请到上海交大的王球老师就带来了一个分析哲学的报告,“人工智能有自我知识吗?”而我成了与他“搏斗”的先锋(评论人)。
不过其实我认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一般来说是搏斗不起来的。为什么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往往聊不到一块儿呢?因为分析哲学家们可以迅速地把问题拆分、析出,所谓条分缕析,最后选取并聚焦到一个小部分去进行讨论。问题拆得越细,大家讨论得就能越有针对性。比如打之前先区分好75公斤级,80公斤级,85公斤级……分得非常细,那么上台切磋的时候双方都差不多,那就能打到一块儿去。
但麻烦的是,分析哲学家刚开始拆分第一步,现象学家可能就不同意了,于是问题拆不细。所以分析哲学家之间争论问题往往能拳拳到肉,但现象学家一张口就云山雾绕,非得从非常笼统、模糊的地方出发。不是说分析哲学家一定就更高明或更肤浅,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风格吧。
王老师的这篇文章也是先拆分出一个问题领域,他在详细展开讨论之前就对全文将要针对的问题做了一个限定——首先,所谓“自我知识”,似乎就是指“主体对于自身心理状态的内省内容”,然后这种内容又分了两类,一是现象性的感知和情绪,二是作为命题态度的信念和欲望,最后王老师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了第二种。
但这个分拆我就很不满意,首先,把自我知识默认为对心理状态的内省,我就不同意,现象学眼中的“自我”是连皮带肉的,“我的身体”是绝对不能省略的成分,我们宁可省略心理谈身理,也不能略过身理谈心理,因为身体在存在论或知识论上都是某种更加基础的东西。
比如我知道我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或者一个残疾人,他知道他只有一个眼睛,这算不算“自我知识”。又比如我知道我额头上贴着一块膏药,这算不算自我知识?我认为,当然算,而且非常重要。我知道我头上贴了纸,和我知道张三或李四头上贴了纸,这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知道很多实验,比如要测试婴儿或动物的自我认知,用镜子做实验,就是在动物头上贴个东西,让他照镜子,他一照,认识到自己头上有东西,拿手或爪子一摸一撕,这就说明他有自我认识。这个实验虽然我批评它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但多少能提示出两点问题:第一,身体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自我知识;第二,获取新的自我知识不一定是通过内省,照镜子之类向外观瞧的活动也是自我知识得以建立的重要环节。
身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通常是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主体与客体的交界处。
许多文艺作品里,主人公在经历梦境、迷幻、穿越、重生之类的情节时,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往往也是看自己的手——这是我的手吗?在这里手就是自我与世界的第一“界面”,是自我的最前线与世界的最前沿,是“第一面镜子”。被注视的双手是“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客体的我”的原初汇合。
注视双手,其实就是注视我的“意志”或者说,就是注视我的“心理状态”,我想要并拢手指,于是我看到了手指的并拢——这不是看到了张三李四的并拢的手指,而是看到了“我并拢手指”,看到了“我想”。我的内在的意志外化、具象化、在场化,我的这个“想要”被我看见了。在我之外与我打了照面。在这个照面中,我确认了这是我的意志,这是我的身体。
斯蒂格勒讲到,记忆之为记忆,它需要通过身体或技术,滞留在我们“外面”,再反过来被认知,这才能形成记忆。我们在讨论自我知识的时候,不能忽略掉身体和技术,只有把自己延伸到“外面”,自我知识才有可能形成。
再下一层的区分也很成问题,现象、感知、情绪,与命题、信念、欲望相对立,看起来貌似是分析哲学擅长后一块,现象学擅长前一块了。其实不然,现象学家讲本质直观,这个感知里头是有结构、有沉淀的,你的信念和欲望都会沉淀在你的感知活动里头,反过来,命题和信念并不是非情绪或无情绪,按照海德格尔来说,现身情态是最源始的,而“命题态度”无非也是一种“情态”,“冷酷无情”也是一种情绪。情绪和命题,感知和信念,都是纠缠在一起的问题。
回到AI问题,王老师说“若AI的自我知识可以讨论,也只能是关于命题态度的自我知识”,但在我看来,最核心的,首先要讨论的,其实是AI的身体问题。AI与人的最大区别,未必是神经系统的区别,而可能是身体的区别。我们说到,人的身体其实是内与外,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原初界面,我们必须在这种界面中才能获取对自我的认识,当然这个界面还可以通过技术延伸出去或收缩回来,但收放之间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归宿。但对AI来说,它的“内”与“外”的界面在哪呢?在键盘上还是在音箱上呢?
人类确认自我的时候,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捏捏脸,照照镜子,但AI可能通过哪一个动作,来接触自我呢?计算机程序的特点是,它可以用程序去读程序,在电脑内存里自己读自己的数据,这只有“内”而没有外,而电脑程序算完之后输出出去,这就只有“外”而没有内。而像人的身体那样,在内与外的暧昧交融的地带,既内也外,内外相照面,这样的位置,对AI来说究竟在哪里,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其实相信AI可能拥有自我知识,但AI自我的构建,要害在于AI“身体”的构建。
三、斯蒂格勒的轮回
我点评的第二篇报告是舒老师关于斯蒂格勒的论文。舒老师的论文又犯了老毛病:把书读反了。但这次他得出的许多结论,的确与斯蒂格勒“不约而同”,他把许多斯蒂格勒其实认同的论证,拿来反驳斯蒂格勒了。舒老师表示,他确实很喜欢斯蒂格勒,所以我的批评他能够接受。这意味着斯蒂格勒比他原先认为的更加符合他的心意。
为了作点评,我专门找来《技术与时间I》重新翻阅,引来对照。在这里我就不再贴舒老师文章中误会的说法了,不过把我找的几段斯蒂格勒的引文贴出来(都是引自《技术与时间I》2000年的中译本)
“由于它是自己的起源——自身包含了最初的原型,思维的灵魂不从外界获得任何东西,它在自身之中找回一切,它是一种自我运动,这恰恰是技术物体不具备的。……西蒙栋是否也向我们陈述了类似的观点?当然不是。……自我运动是不存在的,运动只能产生在异质事物之间。”(117页)——斯蒂格勒反对柏拉图的“灵魂自我运动”理论,把灵魂的“轮回”重新解读为向技术的外化。所谓的“异质事物”就是技术。“大脑皮层投影在岩石中,岩石恰似大脑原初的镜子,这种原初的投影……实现于由东非人向新人过渡的几十万年之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石器开始形成……问题的矛盾性就在于,我们必须讨论所谓的外在化,然而却不存在一个先于外在的内在,内在本身也构成在外在之中。”(166页)“……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内在不可能先于外在而存在,内在和外在都在同一个运动中构成,……二者相互发明。”(167页)
四、现象学不是文化批判
晋世翔和张东林带来了一篇合作论文,非常有意思,从古希腊数学为什么没有“分数”讲起,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数学对待“数”的不同态度,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看作是灵魂上升的道路之一,因此必须参照理念的要求,而非现实计算的要求,去学习数学,在这个意义上1的单元是绝对不能拆分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数学观才为现代数学打开了缺口。现代数学名义上是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但这种柏拉图主义只是在表面上复兴了对数学的高扬态度,但在实质精神上却恰恰背离了柏拉图。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现代人其实是把现实世界复兴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把柏拉图那里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混在了一起,所以所谓的“上升之路”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除此之外,张东林师兄在前一个报告的点评中,还带来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个批评不只是针对前一个报告人(陶老师),更是针对我们整个会议几乎所有老师的风气。
对于这个批评,我也非常认同,私下和张秋成老师聊了很多,他也是非常认同(但在一些细节上观点不完全一样),我在这里就完全用我自己的语言来重新提出这一批评了。
这个批评就是:“现象学不是文化批判”。很多学者以现象学的名义做的研究,无非是讲一讲古代人思维是什么样的,现代人思维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机械化、数学化了,然后,批判一下现代人单向度的思维,完了。戛然而止。
好的文章也许让人看得意犹未尽,而一般的文章也就是“不过如此”。写到这一步,写得再精彩,无非也就是文化批判家的水平,够不够挺直腰杆说自己是“哲学家”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现象学要关注的,不是,或者说不只是批判现代性文化,现象学的基本特色是“寻根”,是追究起源。当我们揭示出某种现代性思维多么地机械化或数学化或怎么怎么僵化的时候,还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奇特的思维究竟是“何以可能”的?既然说这种思维与生活世界如此疏远,那它又如何可能理所当然地被科学家或现代人接受呢?这里头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历史性准备是什么?去追究这些问题,才是现象学能够大展拳脚的舞台。
但很多学者满足于批判,却疏于寻根,这便充其量只是一个受到现象学启发的文化批判家。当然了,拿这一批评来针对我们会议的全体学者,是不公平的,因为很多参会学者确实就不是现象学家,确实就是受现象学启发的文化批判家、STS研究者或一般的教师,他们也没有说都要做哲学家,都要做现象学家。不过作为一个“高要求”,作为我们应当去尽量学习的研究范式,胡塞尔、海德格尔、雅各布·克莱因他们的寻根态度确实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五、两种文化之争过时了
除了指定的评论之外,在自由讨论中我也还算积极地插过几次话,一次就是李恒威老师报告的“认知哲学——再启两种文化的对话”。许多其他老师也提出了批评,认为李老师提出的这个进路压根不是什么融合的第三种文化,而就完全是科学主义文化。而我的问题则在另一个层面上:我认为所谓两种文化的斗争早已过时了,提出两种文化分裂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所谓文化基本上还是“精英文化”,学者们的身份地位大家都看得起,但两拨学者互相看不起(你没看过莎士比亚,粗鄙!你不懂熵增定律,愚蠢!),就吵了起来,在大众面前争一个话语权。但是现在的文化环境是,大众文化才是主流,人们争的是究竟喜欢霸道总裁还是小鲜肉,究竟是追捧大富豪还是大明星,谁来管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是小众文化,在大众眼里都是看不起的。在这种环境下还争斗个啥呢?
当然,很多人讨论两种文化,其实都变成了讨论“两种思维”、“两种态度”、“两种研究方法”、“两种世界观”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偏题的。既然谈所谓“文化”,总还是要围绕着文化谈。
六、VR、艺术与游戏
另一段插话是在邵艳梅报告“虚拟现实技术中的艺术问题”。邵艳梅提出VR艺术的特点是与技术相融合,我顺着邓波老师的批评,认为她是完全混淆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技术创作过程中需要用到高明的技术手段,比如画画需要生产颜料,摄影需要生产相机,VR需要头盔和程序的支持,在这方面技术的介入并不是什么特色。但是就艺术作品本身而言,VR反而可以说代表着技术与艺术相分离的一个新的高度。一个青花瓷可以当艺术品欣赏,但也可以拿起来用来喝汤或储物,一个肖像画可以用来欣赏,也可以被用来展示人物的面相。“可以用来作……”指向某种外在目的的,就是技术器具,而“无用的”,或者说只是”用来“观看、欣赏、把玩等等内在目的的,就是艺术作品。在达芬奇以前,基本没有独立自足的艺术作品或艺术活动,脱离外在用途的”纯粹的“艺术领域,是现代才开始兴起的。而就VR作品而言,它整个建立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从而与”现实世界“更进一步地划清界限,在这种意义上,VR艺术是更无用的,或者说更与技术相分离的艺术。
但说起“融合”,我倒是想说,VR可能标志着“艺术与游戏”的融合。所谓“无用之用”,首先就是游戏的特征,所谓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游戏的一支。而艺术与游戏的同源关系由于艺术的地位被不断拔高而分裂开来。VR的时代,也许恰是二者重新联结的标志。
古代人讲“玩物丧志”,讲的往往就是沉浸于“欣赏”(最初的典故似乎是卫懿公沉迷于欣赏鹤的高雅),又或者沉迷于把玩某些我们现代人称之为艺术品或工艺品的玩意;而现代人“玩物丧志”,往往就是讲沉迷于游戏了。但现代人的玩具和游戏,恰恰只是那些因为互动性强而未能被拔高的“艺术”,又或者说现代的艺术,只是那些看起来更加沉稳冷酷的“玩具”。艺术品无非是某种“观赏性玩具”,而玩具无非是某种“互动性艺术品”。
人与艺术品的关系,最初可能是“把玩”这个动作;而在近代,“静静观赏”这个动作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头有视觉中心主义的影响);到了今天,如果电子艺术或VR艺术真的能够提供某种全新的艺术形式的话,那么互动性和参与性一定会被重新引回来,人和艺术的关系又将从“把玩”、“观赏”,转变为新的形式——“进入”。
顺便说一下,我原定的参会论文就叫做“玩具现象学——论‘玩物丧志’”。结果没写出来,但包括了一些以上提到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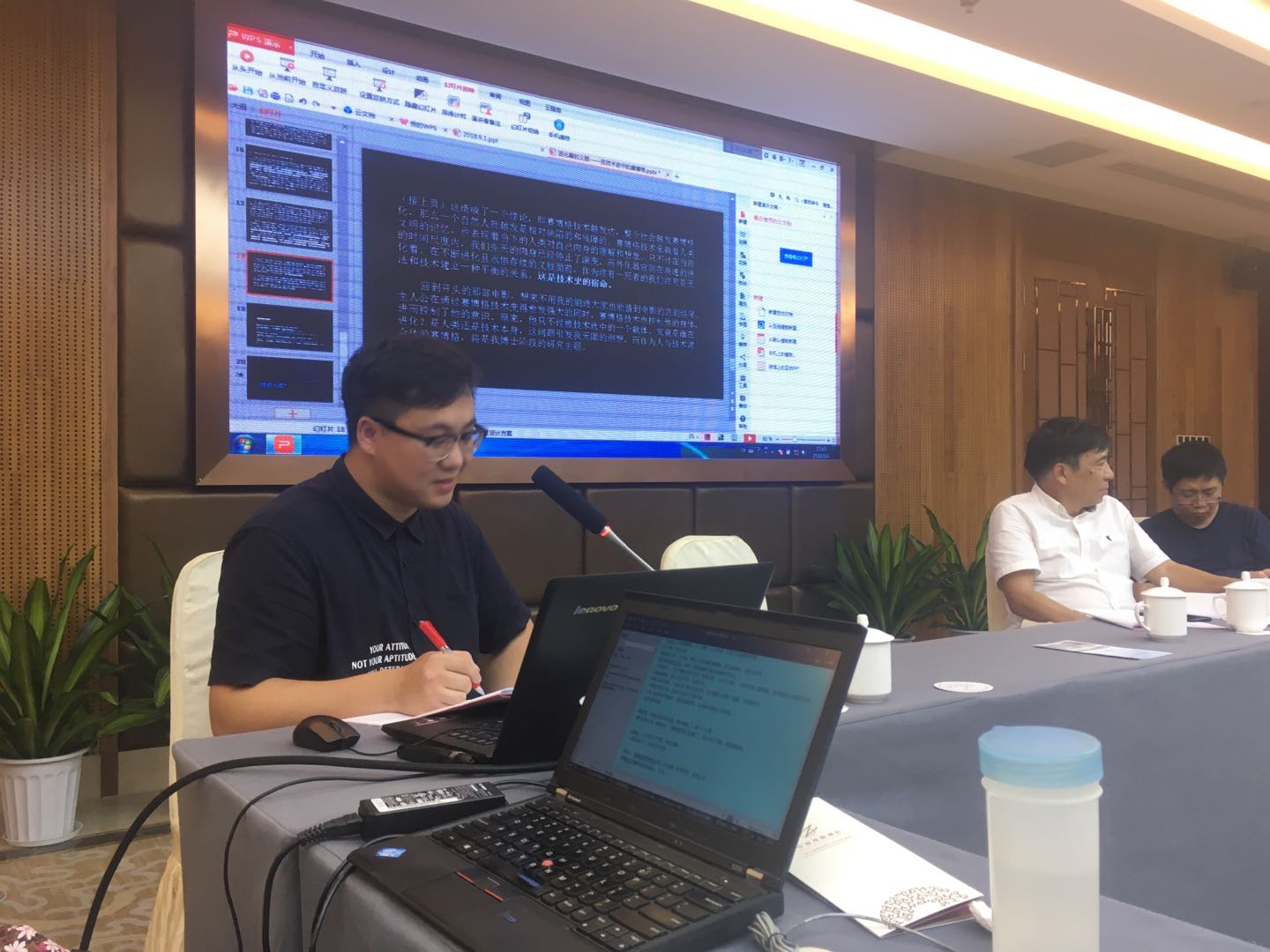
老师写的很好呀,我很赞同张老师和您的观点。所谓深度学习必然包括数据的选择,虽然开始是我们人工设置,使得机器选择错误后就会不断修正,但随着机器修正次数越多,机器就会自我选择“他”认为有用的数据,对数据有一种“敏感性”,所以。机器虽然是处理的数据,但处理数据的方式是有“他们”自己选择成分,选择哪些数据?怎么进行选择的?可能开始是根据着程序走的,但是后期肯定是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