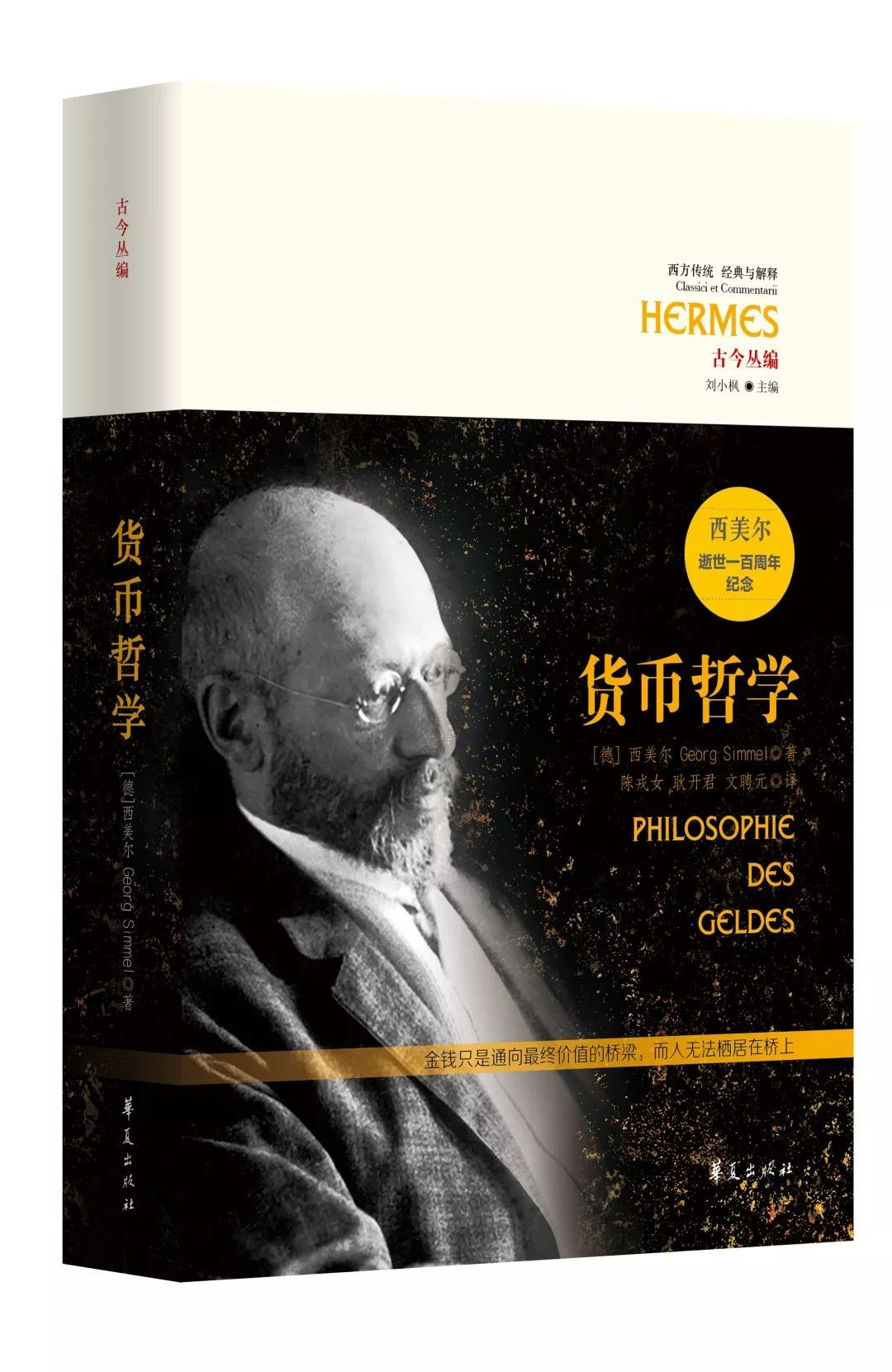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转载请与杂志社联系,引用格式如下:胡翌霖.从《货币哲学》看NFT的价值[J].中国图书评论,2022(12):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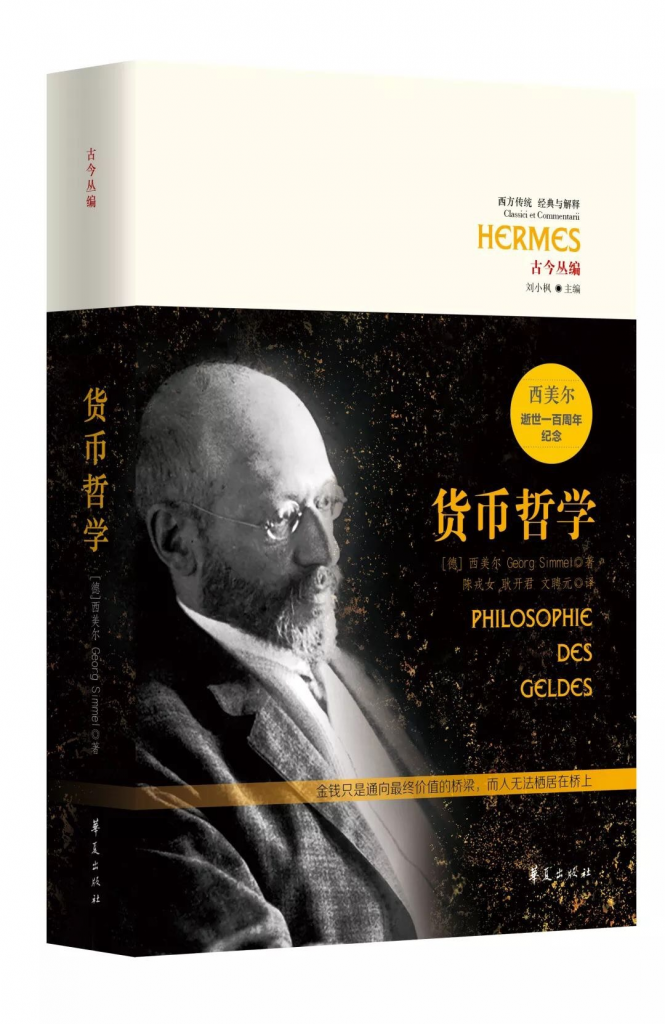
导读:齐美尔的《货币哲学》阐发了一种相对主义版的康德先验哲学,用“距离化”解释价值的由来,用交换活动解释客观性的形成。齐美尔批判现代货币经济颠倒了工具和目的,财产占有与主体的自由脱离了关系。在齐美尔的视野下,区块链支持下的加密货币或NFT,似乎蕴含着帮助人们重塑价值观的某些契机,促使人们回忆起价值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并从占有中发现自我的个性,让人们从现代性的迷惘中醒觉。
关键词:齐美尔、货币哲学、NFT
一、价值的先验哲学
《货币哲学》[1]是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的代表作,这部出版于1900年的奇书至今仍是“货币哲学”这一主题下的经典,甚至可以为虚拟货币或NFT的价值问题提供启发。不过这部书不容易读通,因为它实质上一部带有古典风格的大部头哲学专著,这部书的立意不在于分析货币问题本身,而是以货币为切入点,讨论最深沉和最终极的哲学问题。正如“科勒(Frischeisen-Kohler)认为,《货币哲学》的确关心货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层面:‘但其最终的目标要高得多,如齐美尔自己所言,其最终的目标是以外在的经济事件为材料,探究人性的终极价值及其意义。’”[2]约尔(Karl Joel)认为,“货币对齐美尔来说绝非仅仅是货币,而是世界的一个象征” [2]。特纳(Bryan Turner)认为齐美尔“致力发展的是‘货币’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货币哲学》是对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根源的经典研究。”[3]
所谓的“现代意识”并不是指现代人关于货币的意识,而是指现代人关于人性和世界的意识,货币经济一方面是现代意识的外化体现,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现代意识的某种根源。货币经济和现代意识是互相塑造、互相成就的。
齐美尔把货币这种历史性的、物质性、政治经济层面的东西,看作意识和观念的源泉,这是他与古典哲学相区别的地方。在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先验性通常与先天性绑在一起——先验指的是使得经验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康德认为意识的先验条件就是人类先天的能力,例如感官的空间性和时间性。
齐美尔继承了康德先验哲学的风格,即追问“使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是这种条件未必是内在的、固定的,也可能是外在的、历史性的。晚近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思想可以为齐美尔提供支持。斯蒂格勒重新回应先验问题,指出作为先验条件的认识形式并非悬浮空中的永恒之物,而是根植于作为“第三记忆”的技术世界[4],记忆的媒介承载着记忆的形式。人的认知能力在刚出生时并未完善,当人们在后天学习和认知这个世界时,他们从外在的技术媒介中习得了这些形式,补全了自己的认知能力,而不同的外在环境所塑造的认知方式是不同的,例如书写技术改变了人们思考概念的方式,录音技术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方式。这些外在的技术环境反过来形塑着人们的认知形式,货币也不例外,它是价值观念的外化,也决定了人们认知价值的方式。
如果说“认识形式”即是所谓“先验”,那么这些技术世界的现实发展又是先验的经验根源。齐美尔既追寻“经验的先验条件”,又要追寻“先验的经验根源”,他说道:“许多以前被视作是先验的,以后就被认作是经验的与历史的结构。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任务,即在每一种现象中,在感觉印象提供的内容之外,追寻内容藉之得以形成的、永恒的先验准则。但另一方面,格言说我们应该试图把每一单独的先验回溯到其在经验中的根源处。”[1]51
齐美尔开篇就引入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他首先把“价值”与“存在”相对应。[1]4康德关注的是关于存在的认识何以可能,探讨对存在的经验,而齐美尔在这里要关注“价值何以可能”,追问对价值的需要,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结构:
“就像康德已经说过的:经验的可能性就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因为有经验就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从感觉印象中创造了对象。以同样的方式,需要的可能性就是需要对象的可能性。对象因而就形成了,它的特性是通过与主体的分离而被赋予的,主体同时建立它并且试图以他的欲求征服它,对我们而言这就是价值。”[1]10
康德哲学综合了之前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前者认为知识的根基在主体(我思),后者认为主体是块白板,而知识的根基在于客体。而康德认为知识既不基于主体也不基于客体,而是基于主体如何构建客体的认识形式。类似地,齐美尔认为,价值也不是源自主体或客体的任何一端,“既不能从主体,也不能从客体中得来……它处于我们与客体之间。”[1]11
二、价值源于距离
价值形成于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拉开距离的方式。“客体作为某种被欲求的东西站立在主体的对立面,并且惟有通过克服距离、障碍与困难才能得到它。” [1]10
齐美尔延续了康德的“物自身”学说,认为人不可能对纯粹的事物本身产生认识。所谓的“现实”从一开始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的某种混沌未分的状态[1]7。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由“距离化”造成的,当我们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中遭遇了各种“阻滞”,同时又渴望克服这些阻滞时,“距离”就出现了,而被距离隔开的主体与客体也各自显明,得以被认识了。齐美尔说道:“现实屈从于我们的意识产生变形,这种变形确乎是我们与现实的直接存在之间的屏障,但同时也是认识现实、再现现实的先决条件。” [1]385
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来说,“距离化”就是“去—远”(Ent-fernen),是通过“使之远离”而“得以切近”,海德格尔说道:“移走某种东西以使它离开得远只是去远的一种特定的、实际的样式罢了。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此在本质上就是有所去远的,它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让向来存在着的东西到近处来照面。”[5]比方说,鼻梁上的眼镜并不是认识的客体,而把眼镜拿远审视时,眼镜才成为切近的客体。看不见摸不着的粉尘哪怕近在眼前也不构成认识的客体,而把它搁在玻璃片中透过复杂的镜片组合去观察时,它才成为认识的客体。
简单来说,只有找到某种恰当的“距离化”方式,客体才能够站在主体面前被认识和追求。这种距离有时是单纯的空间距离,有时则是恰当的技术装备、媒介平台等等。
就“价值”而言,“距离化”需要通过“交换”或者说“经济活动”产生。齐美尔说道:
“作为距离化(通过辛劳、放弃、牺牲)的经济活动,同时也克服距离。建立距离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它,令我们与客体分离的渴望、努力与牺牲同样令我们朝它们走去。远离与接近在实践上是两个互补的概念,其中每一个都假定了另一个,它们是我们与客体关系的两面,我们称之为主观上是我们的需要而客观上是它们的价值。为了再一次欲求它,我们不得不使客体离我们更远一些。” [1]17
海德格尔和齐美尔都主张这个“远离与接近互相定义”的辩证法,这乍听起来似乎玄虚晦涩,不过就经济活动而言,其实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在人类茹毛饮血,天生地养的时代,水和食物都不会被看作有价值的商品。只有当人类通过建造,使得自己在空间上离水源更远时,水才会被看作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当人类通过耕作,使自己在时间上离食物更远时,粮食才会被看作有价值的东西。除了这些动物也有的需求之外,人类更多的需求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生食也能充饥,但人们非要发明各种烹饪方法和调味料,让准备食材变得更加辛劳和繁琐,然后再发明各种节省这些繁琐过程的器具。那些节省劳动的器具之所以有价值,依赖于这些劳动被我们额外建立起来。
人类的生活世界之所以越来越丰富,正是因为人类最能自我“折腾”。其它动物的生存主要只是面对大自然赋予的种种阻碍,而人类不同,人类除了应付大自然之外,越来越多的精力和创造力都花在为自己创造新的阻碍然后克服之。
在齐美尔看来,“距离”是某种比主体和客体更基础的东西,客体通过距离才能被认识,而主体也只有在距离中才能认识自身。一个人如果做任何事情都毫无阻滞,言出法随、心想事成,那么他从哪里形成他的欲望和理想呢?所以“距离”的创造和克服不但影响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式,也决定着人类的自我认识。人对自己的定位和认知,对未来的筹划和期待,对生活和工作的意义的理解,都和人类创造出的各种距离有关。
三、价值的相对论
我们看到,“距离”不是亘古不变的绝对存在,不同历史环境和不同的人际关系下,每个人需要面对和克服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距离”既不是绝对客观的,也不是完全主观的。居住地到水源地在物理空间的意义上或许有一个客观的距离,但从价值的意义上,居民与水源的“距离”还取决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愿望、对运输手段的利用方式,人际合作和组织的形式等等。
事实上,如果对价值的认知如果没有主观性,“交换”就不可能发生,但如果完全没有客观性,那么“市场”也不可能形成。
比如张三用一头牛和李四换了十只羊,那么对张三而言十只羊肯定比一头牛更值,而在李四看来反之,这一头牛更值得。双方对价值的判断并不一致,每个人都换到了相对他自己而言更值得的东西,交换才得以发生。
但另一方面,交换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人们虽然对各种事物的价值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但在普遍的交换活动中,公共的尺度逐渐形成。李四愿意用十只羊换一头牛,王五愿意用十一只羊换一头牛……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充分,那么价值的比较就会逐渐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于是,随着源于主观差异的交换活动的普遍开展,最终形成了“客观”的价值尺度。
齐美尔说到:“一个对象必得与另一个对象交换的事实指出了它不但对于我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价值是独立于我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另外的人也是有价值的。这个等式: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在经济价值中找到了最明确的证明。”[1]23
按齐美尔的思路,上述对于“客观性的形成”的解读并不限于价值问题,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其实也是经由某种“知识市场”产生出来的。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为齐美尔提供了佐证。例如有科学史家直接用“交易地带”(trading zones)[6]之类的术语来刻画近代早期科学知识在学者和工匠之间迅速交换的现象。
我们这里重点还是讨论经济活动。随着交换的普遍化,“货币”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货币最初无非是在无数交换活动中最流行、最通用、最受公认的一种交换物。通常也是最容易标准化、定量化的物品。这些公认、通用、标准、定量的交换物就开始成为交换的公共尺度。物物交换让位于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而中性的货币本身去语境化的、去个性化的。有人不喜欢羊有人不喜欢牛,但没有人不喜欢货币。货币的介入掩盖了交换活动中个人的主观偏好和实际情境,大大促进了价值的客观化。
总之,客观性来自主观性,每一笔源于主观好恶的交换活动,在市场中汇总起来,形成了看起来客观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相反,一定要每个事物都存在某种绝对客观的固有价值,然后才可能发生交换活动。
这种观念听起来像是“相对主义”,齐美尔也不讳言。但是他强调这种相对主义并不是消极的“随便怎样都无所谓”,而是积极的,是对真理的严肃追求。他说道:
“相对性并非对一个在其他情况下独立的真理概念而言的一种有所减弱的附加规定性,而是真理自身的一个基本特征。相对性是表象成为真理的那种模式,正如需求的对象成为价值的那种模式一样。相对性并不意味着真理打了折扣,相反,它是对真理概念的一种积极的满足以及使之生效。并非没有相对性,而恰恰是因为相对性,真理才是有效的。[1]53”
“真理是相对的”不是说真理打了折扣,而恰恰是说“真理是可触及的、可遇可求的”。绝对主义者心目中的真理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人类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没有人能保证绝对精确的观察,没有人能掌握绝对完全的信息,所以没有人有绝对的权威来宣称绝对真理就在他手上。结果是所谓的真理就只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信仰”,或者是奖励给胜出者的名号,但不是任何现实的,能够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东西。
而对积极的相对主义来说,真理并不是这种远在天边的东西,而总是相对地存在于当下的东西。真理的可靠性也并不建立在某个空想的支点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交互网络之上。
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仅一步之遥,因为绝对主义把世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都维系在一块不可动摇的铁板之上,那么一旦这一想象中的坚固铁板出现了一点漏洞,绝对主义者的信念就趋于崩塌了。而相对主义者的世界是一张去中心化的网络,零星的破损与纠结并不会妨碍整个世界的确定性。齐美尔说道:“只有那种天真幼稚地坚持绝对的观点才把相对主义置于这样的地位[可靠性的丧失]。但事实上……只有通过把所有那些铁板一块的独立存在消解融化为交互作用,我们才能达到宇宙所有元素的功能的统一,在这里任何一个元素的意义都影响任何一个别的元素。”[1]55
四、现代货币经济的迷失
货币通过“升华事物的相对性”[1]57推动着价值的绝对化。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件,人的价值观念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当然,人们总是希望追求普遍化,就好比说人们总是喜欢市场变得更大、更包容、更丰富。但是,在货币和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主观性和个体性有时被遗忘或歪曲,以至于人们有陷入迷茫和异化的危险。
那么现代的货币经济有何特点呢?齐美尔说道:“对于价值意识来说,货币绝对化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兴趣从原始生产到工业企业这种重要的转型。现代人与古希腊人对钱的态度差别甚大,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货币仅仅用于消费,而现代的货币在本质上效力于生产”。[1]162
这里说的消费与生产的区别似乎令人费解,关键在于,古代货币是某种“最纯粹的工具” [1]140,它本身不是目的,花费它换取商品才是目的。“再没有比货币更明确地象征世界绝对的动态特征的符号了。货币的意义在于被花掉;当货币静止不动时,根据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它就不再成其为货币了。”[1]419
但在现代的观念中,货币变成了“资本”,资本的目的是生产,而生产的目的又是赚取更多资本。“钱生钱”构成了循环,以至于生产什么对象其实并不重要,资本家的目的并不是生产某种商品,而是无论生产什么,能赚钱就行。于是,货币从“最纯粹的工具”蜕变为“最纯粹的目的”。但由于货币中性、客观的特征,这种“目的”刨除了所有主观性和个性,
当这种目的大行其道时,人们真实的、个人的、主观的愿望和追求都“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1]161
当一个人具体的创作、构思、经营和劳动等活动,都以“赚多少钱”来衡量,当一个人做将军、做学者、做探险家等等的理想,都变成“身价多少”来计算,那么人势必会迷失自我。
现代货币经济除了货币本身之外,也把各式各样的“关系”都货币化了。在古代,任何一种“关系”总是存在于现实的能力界限之内,齐美尔说道:“占有一个具有特殊特性的客体——它将意味着比任何抽象的产权观更多的东西——不是可以(好像从外面)直接附着在每一个人身上;毋宁说它存在于主体的力量或品性和客体的力量或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1]232
比如我有一吨大豆,这意味着我在现实中的某个地方储存了它们,我可以把它们拿来喂猪、做菜或播种等等。但是在现代金融体系下,我可能通过某些抽象的票证“拥有”一吨大豆,这一吨大豆我从未见过,也不能拿来炒菜,甚至它们是完全中性的“标准化期货”,压根就不存在任何一堆现实的大豆与之对应,即便在期货“交割”时,它们也不会被现实地摘选出来。
这种“抽象的占有”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色,这种占有赋予占有者的唯一的能力就是可以“卖钱”,而与任何个人的时空位置和现实能力都没有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人只能从它所“占有”的东西那里看到完全中性的、毫无个性的“标价”,而无法找到“自我”的存在。而在齐美尔看来,占有是形成自我的必要步骤。“我是谁”总是由“我有什么”来界定,而“自由”的边界无非就是我能够通过各种外在关系把自我延伸到多远,“只有在已被占有的对象之本质中,自由才发现了自己的局限。” [1]248。
齐美尔说道:“自由就是在对事物的占有中清楚地形成自我。……自我就被所有的‘占有物’围绕着,就像被一个区域范围围绕似的,在占有物中,自我的脾性和性格特征获得了直观有形的现实。占有物形成了自我的延伸,自我只是其中的内核。” [1]246
马克思说过:“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7]这也是在说类似的事情,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在外物中延伸自己,从而能够在外物中确认自己的能力和界限。
而现代货币经济通过货币化,让人占有外物的能力无限地扩展了,同时也是无限地坍缩了。当占有关系完全不受个人的个性或能力的限制而可以无限扩张时,人的贪婪也“无限地膨胀”[1]179了。举例来说,一个贪吃者再怎么贪婪,也不可能24小时无限进食,他对占有食物的欲求受限于他的个人能力,从而不会无限膨胀。但一个贪钱者却完全可以24小时无限地赚钱,因为对钱或者其它任何抽象的占有物的欲求是不受限制的,总是多多益善、永无止境。齐美尔认为,货币这种“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8]
五、区块链重塑价值观
如果齐美尔活到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他也许会更加绝望。因为货币的数字化、客观化、抽象化的趋势更加显著了,货币甚至早已脱离了现实的纸张,彻彻底底成为一个抽象的数字。
那么齐美尔会怎么看2009年区块链诞生之后的加密货币,以及2017年之后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的NFT(非同质化通证)呢?
也许,它们是整个大趋势的进一步延续,貌似加密货币变得更加数字化、抽象化了。但是,我们或许也可能在这些新事物中发现转机。
支持者认为,区块链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去中心化”,所谓去中心化不只是就网络安全的意义上谈论的,而是还带有反权威主义、反基础主义、反绝对主义的意味。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们经常援引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私人货币”[9]理论来为自己辩护。意思是,比特币是否“货币”,并不需要由国家或任何一个官方机构来统一认证,任何人都可以发行或认定货币,只要在私人与私人的交换活动中被互相承认的东西,就可以是货币。
这种货币当然不符合当代对“法定货币”的定义,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回归了货币的本源,让货币的观念回归到主观性和具体的交换活动之中。
比特币和之后的以太坊等加密货币的流行,靠的也不是任何固定的标准或权威的认定,而是重新走了一遍“货币史”,从少数人的交换活动开始扩散其共识,最终形成某种相对客观的价值度量尺度。现在国际上最流行的NFT市场(例如Opensea),其实就已经普遍使用以太币(而非法定货币)作为标价的基准了。
如果说加密货币让人回忆起货币的本源,那么NFT也许是让人回归“所有权”的本源。
NFT可以理解为某种“占有凭证”,通过占有某一NFT,标志着某种所有权关系或者权益凭证。
NFT可以对应于某个会员资格、某件游戏装备、某个契约凭证等等,占有这些NFT意味着某些实际的权力。当然,目前最流行的NFT主要就是一幅数字图片,但即便只是一张小图片,占有这个NFT也并不只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关系。虽然数字图片本身是由抽象的数字构成的,但对它的“占有”关系恰恰未必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NFT是非同质化的,一般来说,每一个NFT都是独此一份,别无分号。同一系列的NFT可能有一些相对公共的价值认同,但实际交易中主观性的存在从来都没有被掩盖。一幅很多人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图片,也许遇到特别喜欢的买家,也可能卖出高价。
当然,目前看来,大部分人买入NFT的目的还是为了低买高卖来“赚钱”,但前文说过,“钱成为纯粹的目的”显然不是区块链造成的文化后果,而是整个现代性的特点。区块链即便能提供转机,也不至于立竿见影。更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买入NFT不是(至少不只是)为了卖掉换钱,而是为了“展示自我”。头像类NFT是目前最火热的类型,这类NFT一般是一个系列数千或一万个适合做头像的图片,每一幅图片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总体上有共享一定的文化或风格。
许多人买入头像类NFT之后,会把它设置为社交媒体账号中的头像。推特甚至已经提供了官方的验证服务,以标识正版的NFT头像,从而与右键下载的图片区分开来。
展示NFT头像,不只是某种“我有钱”的炫耀,更是对自己的审美品味、文化认同、交际关系的彰显。例如Cryptopunk的朋克文化,BAYC的无聊态度,Mfer的自由精神,Azuki的动漫风格等等。在某种意义上,NFT恢复了“占有”的源始意义,使得“通过占有表达自我”成为可能。
当然,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人们本来就喜欢通过设置个性头像来展示自我。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沉迷网络,正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我的归属,而希望在网络世界中找到自我认同。
随便下载一幅图片做头像,和购买NFT做头像有什么区别呢?许多怀疑者认为,如果我想占有一幅数字图片,那么我直接“右键—另存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花高价购买相应的NFT呢?
这种“多此一举”的NFT铸造和购买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人为的“距离化”,创造出一种有待克服的距离,从而孕育出新的价值。
这种经过区块链技术额外“距离化”的对象,和随手另存为的图片,是不同的东西。就好比一幅油画的真迹和复制品,如果只是为了用肉眼欣赏,也许它们没什么区别,但真迹因为稀罕、难以获得,所以就可能有更高的价值。占有NFT和下载图片虽然在肉眼看来完全一样,但是NFT因为难以取得,所以可能被公认有更高的价值。
距离化大大增加了获得NFT的门槛,例如Cryptopunk的占有者永远不会超过1万人,这一系列的头像被人为局限住了,不可能无限扩散,人手一张。这种局限性或许能促进个性化和多样化。例如人们觉得网红脸好看,就可能都去整容或PS,搞成全民网红脸,这是大众文化随波逐流的特性。但如果BAYC成为潮流,那么也不可能全民跟风,更多的风格和文化始终会不断推出。
总之,我们看到,区块链支持下的加密货币或NFT,似乎蕴含着帮助人们重塑价值观的某些契机,促使人们回忆起价值的相对性和主观性,并从占有中发现自我的个性,让人们从现代性的迷惘中醒觉。当然,这也许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无论如何,区块链技术仍方兴未艾,未来的趋势远未尘埃落定,我们总可以努力思考,发掘其潜藏的可能性。
胡翌霖、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基金项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块链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研究”(20CZX012)
参考文献
[1]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美]弗雷司庇.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A].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00.
[3]陈戎女.《货币哲学》译者导言[A].西美尔. 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
[4][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III[M].方尔平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2.
[6]Long, Pamela O., Openness, Secrecy, Authorship: Technical Arts and the Culture of Knowle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
[8][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2.
[9][英]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