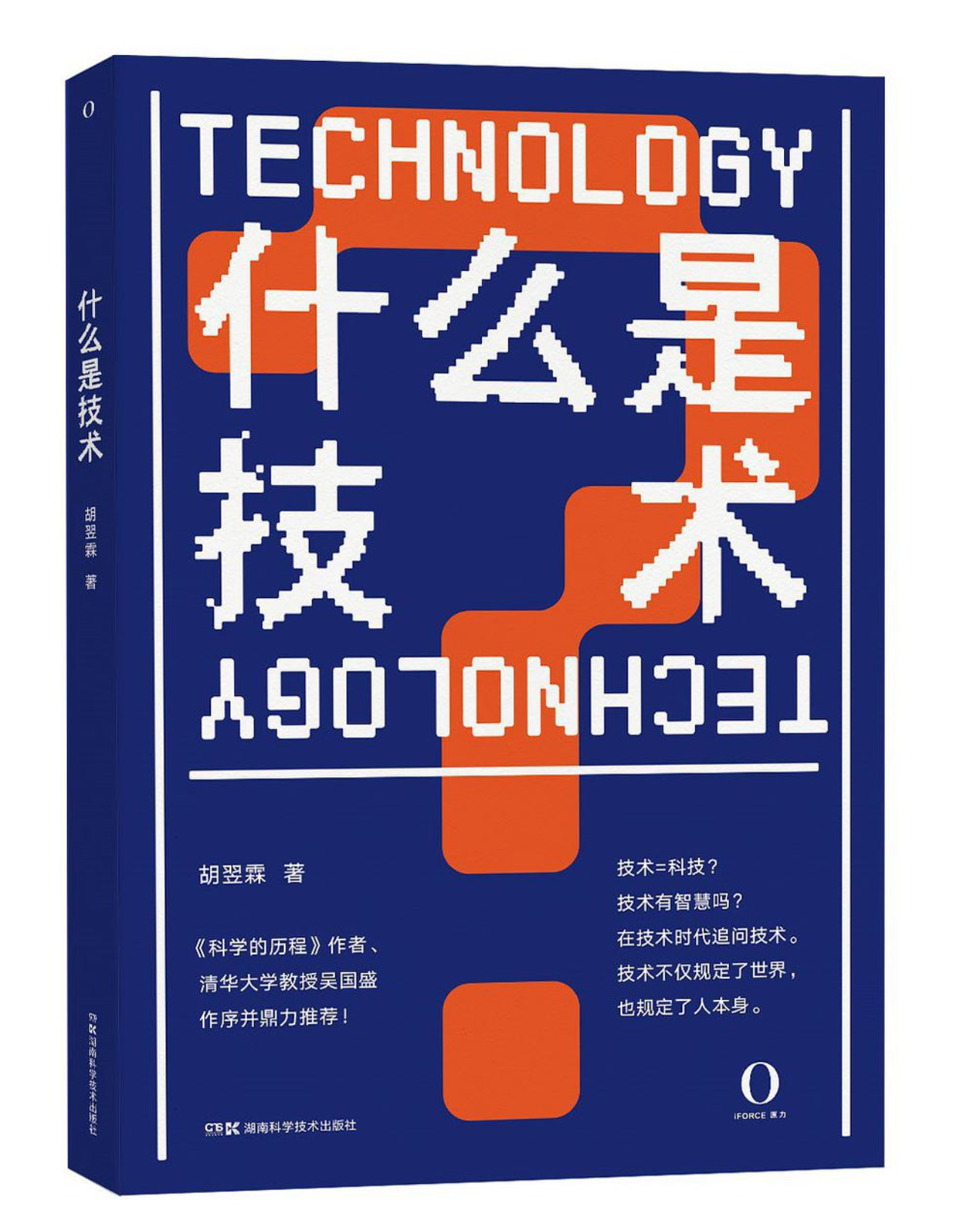感谢《中国科学报》,平时经常约我写书评,这次我自己的书,干脆做了个采访。张文静的采访和整理都做的不错,就是这标题有点咋呼(不过也没办法),成稿见科学网,我这里贴出自己原始的书面回答。

- 首先,想请您谈谈《什么是技术》这本书创作的缘起?您在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正身处一个‘技术时代’。”在技术时代追问“什么是技术”,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这本书的缘起其实没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其中的许多内容其实都是我前些年陆续写作的文章,相当于结集出版,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但我并不想按照文集的体例来出书,所以我以“技术”为主线重新筛选既有文章,再额外新写和改写了一部分内容,整理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
我平时的很多写作都是自发的,不是为了出版或者发表在哪里,写作动力源于个人的求知欲和表达欲吧。我在第一章第3节里写了,如果我不想做“提线木偶”,不想满足于“混吃等死”,我就自然要时时反思自己的处境。
“技术时代”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的大背景,每个人各有各的命运,但总体来说,我们都处于“技术”的支配之下。技术不仅是中性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且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基底,组建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定势。所以简单来说,在技术时代追问技术,就是每个当代人“认识你自己”的基础环节,不追问技术的人,对待自己是不真诚的。
- 本书名为《什么是技术》,但书中其实并未给“技术”提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技术史的梳理和技术哲学的讨论,经由多个视角来讨论对技术的理解。书中各章节看似分散,但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思考过程,比如文字上也多有“前情提示”。为什么用这种写作方式来呈现?
首先你说的“环环相扣的思考过程”有些夸张了,我前面说了,这本书源自于我以往分散写作的若干文章,通过补全和润滑之后结集而成,谈不上是一个连续的思考过程。但我确实是希望以书为载体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
一段表达有多少文字量,与我们如何理解这段表达,是有密切关系的。越是短,我们反而希望它越是精确、越是鲜明。例如说一句“定义”,可能就10个字,我们感觉它很精确,很权威,铁板钉钉的。但其实这句定义的意义需要援引一整套现成的体系才能理解。比如牛顿力学上来给你定义:“力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个定义仿佛是改写了古代哲学家的定义(“力是运动的原因”),但学过科学史就知道这个改变没那么简单。“运动”的概念本身变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运动和变化是同义词),“原因”的概念也变了(从含义丰富的四种原因到位移运动的外在原因),“力”的概念也变了(数学化了)……脱离了每一个词背后蕴含的观念变迁,如果仅仅是拿着10来个字一句“定义”给古代人看,古代人是看不懂的。“定义”之所以有效,是基于我们的整个“时代背景”,基于我们默认的概念配置。但问题是我们要追问的恰好就是这个时代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单纯给予一句定义是没有意义的,更关键的是要去追问这些定义究竟是如何被我们理解的。定义是我追问的起点而非终点。
我们现在社交媒体兴盛,美国是推特治国。微博上一段话100个字,要比定义多,但容纳不了复杂的论证,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立场”之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特或微博上的交流很容易陷入“极化”,非黑即白两极分化,要讨论之前先问你屁股歪没歪,站准了立场才能说话,说出来的话也不看你论证,就看你结论和态度。
1000个字,可以是一篇朋友圈文章。它就可以容纳一些论证和依据了,但又不可能讨论深入,更不可能反映出争鸣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就呈现出快餐式的知识传播。指南、教条之类的东西适合用1000字来传播,除了鲜明的结论之外还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具体化、可操作的套路,比如养生知识。
1万字左右才是一篇正经的学术论文的篇幅,它可以容纳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证,甚至把相反的观点都列在一起互相批判。但一篇论文之所以有效,是需要依托于一个现成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学术共同体之内,同行学者之间,拥有一定的共识,拥有一定的基础训练和公共知识,所以一篇论文可以站在同行和前辈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而代价就是出了圈就不好读了,非但普通人读不懂,非本专业的外行学者也很难进入。
10万字以上,一部著作,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空间”。让非专业的读者也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跟着思路深入其中。我把写书比作构建“园林”,桌子大的空间只能搞盆栽,搞“园林”怎么说都要按亩计吧。园林是有整体性的,只有这种整体性,才能让游客“进入其中”,而不只是在外部俯瞰。但这种整体性又未必是铁板一块的效果,园林内部也是讲究区隔的,不是一目了然统揽全局的,而是一步一景,随着游客的走动而进入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景”有不同的主题,这里是池塘,转完后是奇石,诸如此类。场景既要不断切换,但又不能太突兀或随意,各个场景之间交相辉映。我试图做的所谓前情提示、分环论述,也是试图营造这种分而不散、杂而不乱的整体性,当然未必多么成功,但策略是这样的。
- 豆瓣上也有读者认为,您在书中是不是把“技术”的概念放得太大、太宽泛了。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不是我把“技术”的概念放得太大,而是在这个时代,“技术”的概念就是那么大,我要追问时代背景,放眼望去哪儿都是技术,技术无处不在。我并没有凭空生造出一种“技术”一词的用法,我的用法都是在日常语言中可能见到的。
问题是,很多人满足于找一条确定的定义,然后就自以为把握了技术的概念,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问题。
这种概念的宽泛性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我追问的起点。我恰恰是试图从这种无处不在的宽泛性中,追寻到使得技术成为技术的基本要素,“媒介性”、“可学”之类,都是我尝试性的回答,但根本而言,我们还是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出“技术”概念的统一性,而是必须通过“历史”来理解它。
我开篇就讲到,我们不是通过划定一条现成明确的“国境线”,就理解了“什么是中国”的,我们必须通过历史来理解它。设想说中国统一了全世界,世界上所有的土地都成为“中国”的领土了,那么“中国”一词要怎么理解呢?难道随着最后一块领土的合并,“中国”一词就会一夜之间自动消失吗?现在“技术”就类似于这个处境,在近代以来,“技术”攻城略地,已经支配了生产和生活的全部领域,导致我们很难把技术概念收缩到很明确的一个边界之内,但它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如此支配力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技术史,追究技术及其地位的来龙去脉。
- 这本书虽然涉及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学术领域,但在写法上算是一本通俗著作。您在书中常常用类比等方式消解学术讨论的艰深和枯燥,使文本更具可读性。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出于什么考虑?是您一贯的写作风格吗?把该领域学术前沿内容推给大众的意义何在?您的课堂风格也是如此吗?
首先纠正一点,“学术讨论”并不一定是“艰深和枯燥”的,特别是哲学讨论,它不应该“枯燥”。哲学讨论是激动人心的,很多被认为艰涩的哲学经典,只要读进去了,进入了作者的思想世界,我们会感受到蓬勃的激情。这也是我为什么喜爱哲学的缘故。当然,历史学深入进去,也是很好玩的,比现在的产业化的旅游好玩多了,你去旅游,无非是领略奇风异俗呗,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让我们感到新奇。但读历史就有这个效果,我们能感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各具风采的生活方式,怎么能说枯燥呢?所谓枯燥,可能是在旅途之中必经的一些环节。比如你要去郊游,没有地铁也没有公交,你就得在颠簸崎岖的盘山路上耗费大半天,这段路程是艰难而枯燥的。但有些境地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恰因为它与我们有所隔阂,你要领略美景就必须忍受相应的枯燥路程。
另外,有些趣味是比较高阶的,需要你有知识储备才能理解,储备不够,基础知识不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甚至反感抵触。比如给你讲三国演义华容道的故事,你看到关羽把曹操放了,你如果不知道前情,不知道关羽和曹操曾有恩情,不知道关羽这个人如何看重义气,你就会看得莫名其妙,甚至很气愤,觉得关羽完全是个傻帽,莫名其妙就把敌军大boss放了,简直是不顾大局,根本无法理解关羽在纠结什么问题。你要是不知道桃园结义,直接看到刘备为关羽报仇不顾孙刘联盟亲征江东,你也会莫名其妙。这不是因为三国演义讲得不通俗,而是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有前因后果,没有预先的铺垫,理解起来就很不一样。许多学术问题也是类似,要理解这个问题的纠结之处,你需要预先了解非常多的前情提要,这些前情提要本身其实也都不晦涩,但它们又有更多前情提要。所以普通人直接介入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就会觉得一头雾水,甚至很多基本的词汇都没听说,好比说连孔明和卧龙是一个人都不知道,当然就读不进去、不知所云了。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有糟糕的倾向,技术要故作枯燥、故作高深,以标榜自己的专业地位,我们要避免这种风格。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大众写作,我们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为了更简明、更清晰、更流畅地表达意思。
在所有的学术领域中,哲学是最特殊的一门,因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永远都是“认识你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不断回到“自己”,回到发问者。你做一个工程学研究,你研究完了之后不是讲给自己听的,你是讲给其它同行学者或者干脆是施工队听的,所以根据读者不同,你要用他们最容易接受的语言来讲话。但做哲学,最终是讲给自己听的,要讲给那个发问的自己听的,这就天然地要求我们不是以特定专业的语言来表达,而是回到自己的母语来讲述。
而“我”是一个统一体,我不只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每一个专家同时也都是一个“常人”,专业工作之外更主体的生活方式是日常生活。如果我并不把自己割裂开来,而是把这个日常生活着的自我当作回应对象,那么我就自然要求自己的语言不断回归日常,既从日常语言出发,又最终回归日常语言。与其说我是要把学术研究推给大众,不如说是要把作为学者的自我与作为日常生活者的自我统一起来。
- 在本书之前,您应该是已经出版了四本著作吧?这四本书各自的风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吴国盛老师在序言中说,您是乐于写书胜过写论文,为什么钟情于写书这种方式?
在第2问里讲了,10万字左右的篇幅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思想空间,而论文就很难达到。当然,吴老师序言里的说法其实有点是敲打我的意思,因为我发表论文有些迟缓,他希望我分一些精力出来多发几篇论文,这也是应该的,我正在努力。之前的几本著作大致是这样的,第一本《科学文化史话》是我研究生期间的作品,在博士毕业前后结集出版,相对松散和稚嫩,所以我现在一般也不爱提他。《媒介史强纲领》是我博士论文整理而来,目的是把媒介环境学引入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视域,我觉得有一定学术价值。《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和《人的延伸——技术通史》分别是我开设“科学通史”和“技术通史”课程的成果,反映了我课堂讲义的风格。《过时的智慧》相对完整,把一学期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了。而《人的延伸》是一个截选浓缩版,是技术通史课的精华部分,先出一本试水,然后更加全面和丰富的技术史著作我正在写作中。
- 看到书名《什么是技术》,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吴国盛老师的《什么是科学》。与作为舶来品的科学相比,面对国内读者阐述“什么是技术”,有没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难点?
其实我认为“技术”也同样的“舶来品”,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技”、“艺”、“术”、“法”、“式”、“工”、“器”等等一大串相关概念,但是并没有与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技术”一词恰好对应的概念。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实存,和我们思想观念中的“技术”观念,都不是中国固有的,和“科学”一样,都是“舶来品”。
因为在今天,技术的含义更加宽泛,造成了我们更容易把它当作一种普世的、一般的、中立的概念,这种中立视角甚至比面对“科学”更加顽固。在包括吴老师在内的几代学者的努力下,现在我们越来越能够接受“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传统。但即便吴老师本人,在“技术”是否普世的理解上也与我有分歧。这可能就是相比于讨论“什么是科学”,讨论“什么是技术”更难的地方。因为“技术”过于宽泛,导致我们可以具体地讨论某种技术,但很难把作为总体的“技术”当作反思对象。
作为总体的“技术”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实存层面的“技术环境”、“技术系统”,二是观念层面的“技术”的概念。我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技术和科学一样,都有其整体性和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需要在技术哲学的指引下通过技术史的追溯勾勒出来。我现在的这本书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 能否请您举几例说说,书中您提出的比较有独创性的新观点,是哪些呢?
我不知道你所谓“独创性的新观点”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每一个“观点”,几乎都不会是全新的。学术史上肯定有别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提出过。追求所谓的“全新独创”,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外行的理解方式。
当然,学术需要有新意,要贡献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很难用三言两语的观点概括出来。比如“光是粒子”,牛顿也提过,爱因斯坦又要提,但他们提这个观点的语境完全不一样,在学术界产生的意义也完全不同。
就这本书而言,如果非要我自吹一下所谓独到之处,我也不觉得是具体的观点,不如说是视角和方法。首先就是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相结合的视角,其次是一种现象学的运思方法。但这些并没有作为结论性的东西在正文中体现。
非要讲观点的话,我认为关于“技术保护区”的设想是比较新鲜的,最后的“西体中用”的思路也是相对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