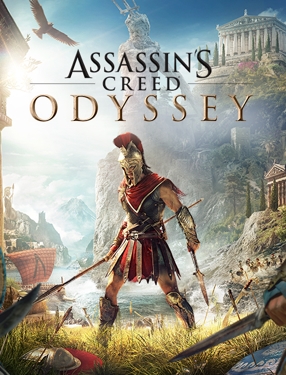为柳帆护士强行辟谣惹人愤怒。所谓的谣言触怒了某些人,他们怒斥谣言的力量可怕,然后给出了所谓的辟谣,但是这“掷地有声”的辟谣仿佛就是在确证,她是护士没错,她在抗击疫情也没错,她染病去世也没错,她全家染病也没错……错的是什么呢?辟谣者强调,防护服不缺。言外之意是,她有充足的防护条件,不是因为资源紧张而染病,只能是因为自己疏忽而染病。
然后,辟谣视频中一句“她只是个打针的护士”更加让人寒心。仿佛说她一个区区二线护士,自己染病活该,更不配被人哀悼。
其实如果理顺逻辑,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说:物资确实匮乏,直接动手术的医护都缺防护服,她只是个打针的护士,缺少防护是正常的。
然而,他们要一口咬定“物资充足”,从封城时湖北省长宣称“物资充足”开始,官方永远不肯坦陈物资紧缺的状况,甚至对医护人员私人发布求助信息百般打压,千方百计就是不允许说物资困难。
但这种坚持究竟是图啥呢?疫情汹涌,物资紧缺,这是客观事实,正因为条件困难、情势艰巨,才需要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但为什么在面对艰难的处境时,那些人还非得强调一切顺利呢?
这种悖谬的态度,其实已经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们随便看看那些抗日神剧就能知道,那些剧本总是把我方的力量塑造得极为强大, 我军不缺枪不缺粮还会武术,而敌军又蠢又笨又无能。结果一些神剧甚至让观众们困惑:日本鬼子是怎么在中国坚持八年的?
我在中学时代读哲学课时也有这种感觉,课本和老师都把所谓的唯心主义者们讲述得极为蠢笨、荒唐,好像随便一个中学生都能把他们驳得体无完肤。但是同时又要说唯物主义是如何曲折取胜的。
这里头有一个基本的悖论,那就是,当你在贬低敌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贬低你自己。如果敌人如此不堪一击,而你又需要那么艰难奋斗才能取胜,那么就说明你也强不到哪儿去。费力才能胜过弱智的人多半也是弱智。
当然,“敌人”未必是具体的人物,抗击病毒、地震、洪灾等等,也是类似,敌方来势汹汹+我方条件艰苦,凸显出我方的英勇;反之,敌方毫不可怕+我方条件充裕,然后再打得丢盔卸甲,这更加显示我方无能。
但这么简单的道理,要认清楚并不容易,进而,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去贬低反而拔高敌人,这就更难以做到了。
所谓“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当然是对敌人的恰当态度,但是这种态度莫说在实战中很难贯彻,等到了“叙事”的层面,就更难以贯彻了。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区分出“战略性叙史”与“战术性叙史”?
我们一直提的“先验历史与实际历史”似乎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区分,先验历史或意向历史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某种宏大趋势,但在实际历史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最终被战胜的对手。我们最近在读《技术与时间1》,其中谈到的技术史的“趋势”与“事件”两个层面,也可以作此类比。
科学史领域有“辉格史”与“反辉格史”的概念,辉格史指的就是辉格党的叙事方式:把历史描述为辉格党打败种种对手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历程,把历史叙事当作论证辉格党合法性的工具,又反过来从现有的合法性出发去筛选历史。
关于辉格史历来有很多争论,有些人以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论证“辉格史”是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我们总是要以现代人的立场去重审历史,这也是历史学的意义所在。但另一方面,柯瓦雷、库恩等科学史家确实展示出了反辉格的叙史方法,无非是要回归历史语境,同情地理解古人的思想世界。
我们知道,启发库恩的关键事件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讲述,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问题上显得特别愚蠢,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得意于现代人的高明并蔑视古人的愚蠢,而是努力站到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思考一个如此伟大、如此睿智的人,如何可能得出这些看似愚蠢的观点。
于是,库恩在科学史中发现了“时代”,发现了一个时代的人往往共有某种研究范式。而时代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一次又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睿智战胜愚蠢,因为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被最终战胜的思想,同样也是伟大的,是合理的。 托勒密体系在哥白尼的时代仍然有强大的力量。
柯瓦雷、库恩那里树立起来的,“尊重败者”的叙史策略,被后现代学者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认为压根谈不上所谓胜者和败者,各种世界观应当是不分高下的。后现代进而反对传统叙史者的“宏大叙事”,反对在叙史中加入某种大主题、大线索,消解叙事中主角、主线的存在,让历史碎片化。
简言之,后现代的历史不再有宏大的“战略”层面。但我们能否在接受“尊重败者”的理念的同时,仍然坚持某种宏大叙事呢?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反对辉格式“宏大叙事”,反而是反对它还不够“宏大”。“辉格史”的毛病并不在于它给英雄唱赞歌,而是恰恰在于它唱出的赞歌还不够宏伟。它把英雄战胜的一个个敌人看作是生来就注定灭亡的丑角,把英雄的艰难险阻看作必然能够通过的顺途,那么它所塑造的英雄也谈不上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更宏大的叙事”不但要拔高辉格党,还要拔高托利党,不但要拔高哥白尼,更要拔高托勒密。
我们也许可以仍然承认一种在碎片性的个别事件之上,存在着宏伟的“时代大势”,而在“大势”之下,也存在着伟大的英雄。但同时,大势之所以“大”,是因为时代发生着“剧变”,发生着断裂性的革命;英雄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战胜的对手也如此伟大。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能接受某种“征服自然”之叙事,前提是,“自然”是值得敬畏的对手,人类在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向她发起挑战,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这种叙事看起来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拷打自然),也不是前现代的(顺从自然),也不是后现代的(压根没有自然)。或许与口语时代的英雄史诗最为接近,但相比口头叙事更讲逻辑和条理。
这种比宏大更大的叙事至少是可能的。但它有什么意义呢?至少说,它可以把“意义”本身拯救回来。因为只有通过某种目的或趋势标明方向,才能够衡量意义。先行的死亡让人的行为具有意义,先行的“完成”让历史事件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