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9-08-16 第7版 书评)
“我是谁?”——这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大问题,哲学家们为此殚精竭虑,而现代科学也以不同的角度推进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有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有人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我是一个人”。“我是谁”这一问题立刻被转换为“人是什么”,而绕过了对“一个”的追究。
无论我是什么,我首先是一个“个体”,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埃德·杨的这本微生物学科普书:《我包罗万象》,首先就动摇了这个理所当然的常识,作者借用了惠特曼的诗句“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提出“我”从来不是单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军团”(第4页)
这个“军团”包含有人体的无数细胞和组织,也包含与人体共生的无数微生物。从普通人的视角看,每个人只是一个个体,但是如果我们从从微生物的视角看,“每一个人或动物都是一个长了腿的‘世界’,一个能够和他人互动的移动生态系统。”(第235页)
当我们指着一个人说“一个”时,我们是如何确定个体的边界的呢?是基于空间上的边界,还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呢?然而就空间而言,微生物和我们共处于同一空间,密不可分;从发育成长的连续性而言,动物的发育过程往往需要微生物的参与,如果没有微生物,即便能够发育起来,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个体。
甚至人类引以为豪的“自由意志”,都很难与微生物相切割。近年来科学家提出了“肠—脑轴”的概念(第64页),认为肠道菌群的环境和大脑的反应有直接的关联。例如给小鼠喂食B-frag细菌,会导致小鼠更喜爱探索和交流(第62页),把自闭症儿童的肠道细菌移植给小鼠,会导致小鼠出现重复行为、厌恶交流等等行为。(第63页)
既然微生物如此深刻地参与着每一个“我”的成长过程和机体运转,那么我们就把它们当做自我的“一部分”不就行了?它们就像无数细胞那样,无非是“个体”的“组成部分”,而“个体”始终还是“一个”整体嘛。
但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微生物毕竟确实是外来的“他者”。婴儿出生时从母亲的阴道中获取最初的微生物群,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与外界交互,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微生物内环境。在人体中扎根的微生物,也会在一些情况下(如服用抗生素)被驱逐清除。它们并不像器官或组织那样,确实是个体的相对稳固的“部分”,而是有点像可插可拔的“外设”那样,扮演着某种介乎于自我和他者、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某种角色。
这有点像人类的技术工具,我们依赖它们才能生存,当我们如臂使指地运用工具时,它们仿佛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类比,他认为微生物“犹如电脑、钢笔和刀这样的工具,可以用来创造美妙的作品,也可以唤醒可怕的妄念。”(第74页)
作者试图用工具作类比,解释微生物的“中立性”,即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好细菌”或“坏细菌”,同一种细菌在肠道中可能扮演“好菌”,但进入血液就变成危险分子了。即便是呆在肠道里的好菌,在机体发生某些疾病或失调时也可能随时乘虚而入,让健康进一步恶化。而有一些明确的致病细菌(如导致胃炎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有可能在其它方面具有益处(如防止胃酸反流)。
技术哲学家有可能进一步深化这一类比——技术工具或微生物都不是某种非好极坏的的东西,但也并不是真正“中立”的东西,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自主性”。“技术自主论”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们向人类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让人类尽可能适应于它的偏向。人类不断改造技术环境,而技术环境也不断反过来塑造着人。
微生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微生物是动物的外在环境,同时也是其行为和机能的内在组建者之一。动物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地形塑自己的微生物内环境(第139页),就好比人类总需要通过学习和适应,去改变自己的“工具包”,同时,人类又利用自己的“工具包”去改造外部环境。
作者发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对微生物的依赖性相对不那么强:“奇怪的是,人类会没事,对其他动物而言,彻底灭菌意味着快速死亡,而我们人类却可以坚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第11页)
在我看来,这倒不算奇怪,因为人类对“他者”的依赖性其实是最强的,如果不穿衣服,没有住宅,人在寒冬就坚持不了几天,如果直接茹毛饮血,体质较弱的现代人也很难生存下去。人类在其千百年的进化史中,不仅在不断塑造着与微生物共生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塑造着一个赖以生活的技术环境。因此,当人类的微生物环境被清除时,技术环境仍然能勉强支持人的存活。但如果把人类与之共生的微生物和技术环境统统清除掉,那恐怕就坚持不了几个星期了。
针对“我是谁”这一古老问题,微生物学和技术哲学殊途同归,发现了“个体”并不是某种封闭、孤立的存在者,所谓“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也不是现成固定的。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以“我们”来指称自己了。“我”当然还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当用动态的、生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古代人认为人体这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相似。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看,体内微生物的生态系统,也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系统相似。因此对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深入理解,也有可能启示我们理解动物界的共生关系,乃至于为人际交往问题或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
无论是医治个人还是治理社会,传统的思路是线性的——如果出了毛病,要么是缺了什么有益的东西,要么是多了什么有害的东西。于是解决方案无非是“补药”或“排毒”。人们对待新思潮或新技术的流行,无非也是这两种极端的态度,要么热烈拥抱、视若珍馐,要么反感抵制,视之为洪水猛兽。但微生物学告诉我们,补充一种益生菌有可能挤占其它益生菌的生存空间,消除一种有害菌也可能让更危险的菌趁机上位(第193页)。对于他者,我们应当在拥抱和驱逐之间寻求共生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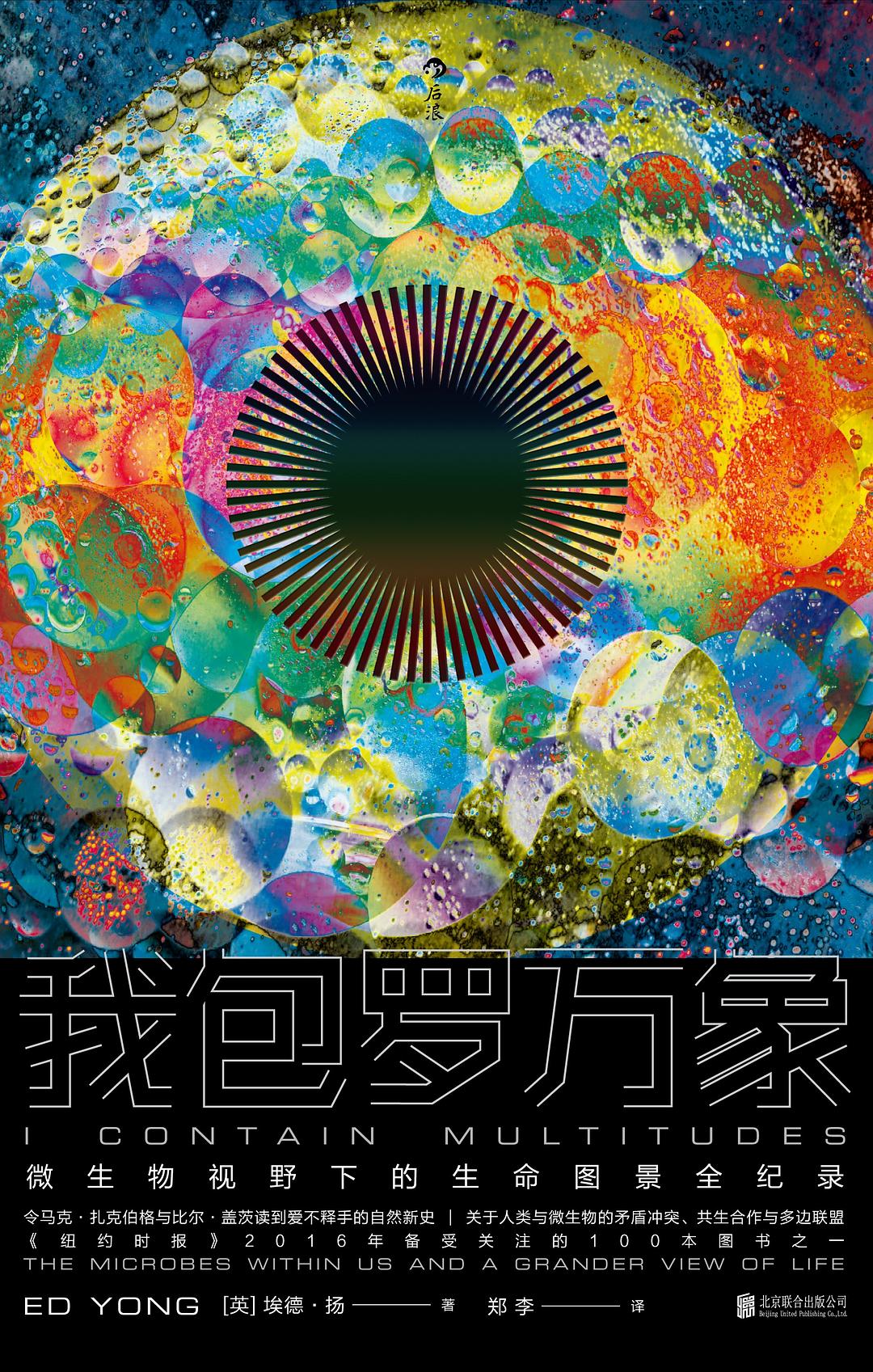

人是“方式”,而不是“什么”。自海德格尔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这类原则上还以本质主义的眼光从不同层面上看待人的科学都不过是让人更远离自身罢了。
就理解人而言,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你所说的什么“一个”,而在于提问的方式。倘若以“X是什么”这种传统哲学(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此后的一切可能的科学)的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那么无论答案是什么,形式上看,答案总是普遍的东西,也即种类或范畴。然后,以此答案为概念C(X是C),把具有符合概念C的特征的个别的东西归为用概念C表达的种类或范畴,也即“X是什么”的答案。所以,“我是人”这句话其实说的是“可以把作为个别的东西的我归为(属于)用人这一普遍的概念表达的种类或范畴”。在这里,根本还没有“一个”这个量词出现的份。“我是人”这句话不会因为少了“一个”这个量词而不成话。
哲学争论的“一”与“多”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你所谓的我是“一”还是“多”。我说得刻薄一点,真正的哲学家根本不会关心你所谓的我是“一”还是“多”,真正的哲学家所关心的“一”与“多”是普遍之“一”与个别之“多”的关系问题,也即共相(普遍的概念)与殊相(个别的事物)的关系问题。而在“我是一个人”这句话中的量词“一个”不过是意味着我作为归为(属于)用人这一普遍的概念表达的种类或范畴的个别的东西的个数的“多少”罢了。
这都哪跟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