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厚度——对梅洛庞蒂施耐德病例的理解[1]
我处理的是《知觉现象学》第一部分第三章的第8小节:“‘象征功能’的生存论基础与疾病的结构”。
从小节的题名就可以看出,这一节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之前的章节中,梅洛庞蒂介绍了施耐德病例,并引入了两种传统的解释进路:机械生理学试图从身体机能的损伤来进行解释,而理智主义心理学试图从意识的层面进行解释。但梅洛庞蒂认为二者都不能真正解释病态的可能性。于是到了这一节,梅洛庞蒂终于要给出他自己的解释了,这一节中,疾病的结构(而不是其原因)将被揭示,这同时也是对意识的生存论结构的揭示。这一节对于前几节来说是总结性的,而对于后文来说则是奠基性的。
经验主义的机械生理学提供的是因果论说明,这种因果论说明也许是准确的,但并不是我们理解疾病所需要的。例如,我们可以把病态的结果归因于一次物理损伤——弹片破坏了他的肉体,损伤了他大脑中某些涉及视觉机能的部分。这一解释毫无问题,但并未满足我们的疑问,即为什么他的疾病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症状并不是单纯的视力衰退,而是丧失了抽象运动的能力——他看得见,也听得见,也能够控制他的身体,但就是无法根据抽象的指令完成一个动作(准确地说,是无法直接完成,必须通过准备运动、反复尝试等迂回的方式完成指令)。机械生理学把身体分解为互相独立的机能或部件,但施耐德病例并不表现为某一特定部件的失效,而是表现为某种整体性的、精神性的障碍。
对施耐德病例的理解必须超过客观的因果分析而进入意识的层面来分析,在这个意义上,“理智主义的反思分析超过了因果思维与实在论”109,145。理智主义不再把施耐德的疾病刻画为某种具体的身体功能的缺失,而是追究到意识的“象征功能”,或者说“投射能力”、“表象功能”,这种功能使得抽象运动成为可能。
“抽象运动不是由任何一个实际的对象所引发……这种无动机的意向指向本己身体,将本己身体构成为对象,而不是穿过身体以便通过身体与诸对象相联系。因此,抽象运动蕴含着一种对象化能力,一种象征功能,一种表象功能,一种投射能力……意识就是这种能力本身。只要有意识,为了能够意识到,就必须有某个意识能意识到的某物,一个意识对象。只有当意识能让自己‘非实在化’并投身于对象之中…… 意识才能趋向这个对象。”106,140-141“这种‘投射’或‘召唤’(在灵媒召唤一个不在场者并让他出现的意义上)功能也是使得抽象运动得以可能的东西。”106,140-141
也就是说,“意识”不是某种实体,或者说一个伫立于客体对面的某种主体,并不是意识通过某种能力把客体召唤到自己面前,而是说意识就是这种召唤能力本身,是这种神秘的“媒介”。梅洛庞蒂所批评的理智主义也已经超越了心物二元论,而是诸如康德的先天感性形式或胡塞尔的意向性——意识不是一个对象,而是指向对象,或者说使对象呈现的媒介。
事实上梅洛庞蒂对这一理智主义的进路持肯定态度,他要做的并不是反叛这一进路,而是对这一进路进行更深的反省,揭示其生存论基础。在这一节开头梅洛庞蒂就说:理智主义的问题“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抽象”109,145。理智主义矫枉过正,过多地局限于意识的层面,而把多样的经验对象完全撇开了,割断了抽象分析所奠基的土壤。因此难以解释经验的多样性和意识的各种形态(和病态)。梅洛庞蒂指出,不能完全撇开“肉体”在疾病现象中扮演的角色——施耐德并不是被弹片击中了“象征意识”,弹片破坏了他的肉体,但当然施耐德的疾病毕竟是精神性的,“他的精神通过视觉而受到损害”。110,146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精神的维度反思施耐德病例,但又不能撇开肉体。
梅洛庞蒂一直都试图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在实在论与理智主义之间,寻找某种“中间”的进路,而施耐德病例也恰好提示出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某种中间环节的缺陷——“他所缺乏的既不是运动性,也不是思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作为第三人称过程的运动和作为运动表象的思维之间,有某种东西——某种通过作为运动能力的身体本身来保证的,对运动结果的预期或把握,有一种‘运动计划’,一种‘运动意向性’;……病人时而思考运动的理想形式,时而用他的身体进行盲目的尝试;相反,在正常人那里,每一个运动既是运动,又是对运动的意识,两者不可分离。我们也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在正常人那里,每一个运动都有一个背景,运动与其背景是‘一个单一整体的诸要素’。运动的背景并不是一个与运动本身外在地联结或关联在一起的表象,它内在于运动,它激发运动,并且每时每刻都在支撑着运动。”96,128
机械生理学和理智主义心理学的进路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把行为夷平在同一层面”108,144—— 要么把行为单纯地置于“形式”的领域来关照,要么置于“内容”的领域来关照。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种运动的形式与运动的内容之分裂恰恰是疾病的症状本身,在正常人那里,“媒介即讯息”,形式和内容,反思和对象化是互相内在于同一个运动之中的,而在施耐德那里,缺失出毛病的并不是二者中的任一个,而恰恰是将二者紧紧地耦合在一起的媒介。
我试图用“媒介的厚度”这一概念来诠释梅洛庞蒂的理路。
所谓媒介,也可以换成“环境”(梅洛庞蒂经常使用的milieu一词既有环境也有中间、媒介的含义),对象通过媒介而呈现,媒介即是把对象带出来的背景,或者说指向对象的“通达”。不过相比“环境”或“背景”等概念, “媒介”一词更为凸显其居间性。媒介或背景具有透明性,当对象通过媒介(在背景中)得以准确地呈现时,背景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似乎是直接看见了对象,而略去了它的背景,然而事实上其背景或媒介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通达对象的必由之路。我们将看到,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空间”即是这样一种媒介,身体既不是思维,也不是对象,而是连接着思维与对象的那个中介,在它的连接下,思维与对象被包裹为一个整体——“身体空间有别于外部空间,它能包裹住而不是展开它的诸部分,因为它是景象的明朗所必须的室内昏暗,是动作及其目的能在其上凸显所必须的模糊的力量储备和沉睡背景,是点、图形和各种精确的存在能在其前面(in front of which)显现的非存在区域。归根结底,之所以我的身体能够是一种‘构形’,之所以会有图形——优先于其无关紧要的背景——在身体前面出现,是因为身体已被它的任务所极化,是因为身体朝向它的任务而存在,是因为身体在它对它的目的的追求中聚为一体,而‘身体图式’最终说来是表达‘我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的某种方式。”87,117
理智主义的进路已经把意识理解为一种媒介,或者说一种以“对象”为终点的射线。但问题是,他们并未考虑这条射线的“厚度”,也就是说,这条射线只有从思维到对象这一个方向,而没有一个内在的空间,于是就不能包含某种阻滞,也无法提供某种回旋余地,意识要么是正确地指向要么就是错乱地指向,而难以设想某种“或多或少地指向”的暧昧情况。梅洛庞蒂指出,理智主义所理解的这种意识“完全透明,这种意向性不承认多或少的程度”,如果从这样的意识概念出发,“一切将我们与真实世界分隔开来的东西(错误、疾病、疯癫,总之,一切肉身化活动)都被归结为仅仅是表面的状态。”“在意识的多样性那里没有任何有待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唯一可理解的东西就是意识的纯粹本质。”109,145也就是说,如果意向性没有厚度,意识的障碍只能在媒介的两端得到理解,于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疾病的多样性。当然,也更不能理解日常知觉的多样性或历史性,因为只有意向的对象是经验的,而意识的形式则只能是先天的。一个弹片,它并没有打中施耐德的象征功能或“先天形式”,而是损伤了它的实际的肉体,而这一损伤如何可能影响他的知觉形式(而不是看不见内容)呢?梅洛庞蒂的理解是,意识的形式和其内容一样,都是现实的、实在的、肉体的——正是这个同时也作为对象的身体,参与着对象的呈现,身体既是对象也是媒介,媒介不是先天的抽象物,它同时也是具体的东西。讯息在媒介中呈现,但媒介本身也是一个实际的讯息,作为大脑机能的意识和作为意向性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对象化的身体和作为媒介的前对象的身体是同一个身体,梅洛庞蒂试图“重建关于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112,147
理智主义难以解释“象征功能”与身体机能的关联,理智主义的理论甚至没有容纳“理智”(理解力)本身。传统的理智主义或许认为,理智能力是一种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范畴的能力,但问题是,施耐德的这一能力并没有消失。施耐德的缺陷并不在于把具体的感知经验归结于一个明确的范畴之下(或者把不同的样本归结于同一个理型),恰恰相反,“他只有通过一种明确的归属才能把这些材料联系起来”112,148。他不能理解“类比”,例如“眼睛与视觉的关系等同于耳朵与听觉的关系”。正常的理智直接能够理解这些类比,相反,施耐德却必须经过某种范畴化、抽象化的澄清过程才可能理解类比,例如他会分析:“眼睛和耳朵都是感觉器官,因此它们应该能产生某种相似的东西”113,149,经过如此这般的分析推演的引导,他才可能“理解”类比关系。
也就是说,正常人的理解力事实上发生于“澄清”或“阐明”之前的某种混沌暧昧的空间之中,而范畴化的抽象分析只是理解过程的一种极端特异化的状态。
“正常的被试之所以能一下子就理解眼睛与视觉的关系等同于耳朵与听觉的关系,这是因为眼睛和耳朵是作为进入同一个世界的手段一下子就被给予他的……以至于这种等价与类比在被构思之前就能被体验到。……实际的主体应该首先拥有一个世界或在世界中存在。也就是说,应该在它自己的周围维持一个意义系统……这个意义系统的各种对应、关系、共享不需要被阐明就能被使用。当我在家里走动时,我无需任何推理就能一下子知道,走向浴室意味着经过卧室,注视窗户意味着壁炉就在我左边……” 114,150
这个事物在得到明确的构思之前,或者说事物在成为界限分明的“对象”之前,作为进入世界的媒介而已然面对的“世界”,就是所谓的身体空间。这一个暧昧的世界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身体作为媒介,所内含的厚度,或者说半透明性。
当我“走向浴室”的时候,“浴室”是我整个意识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然而,这个“指向”绝非是毫无保留的,在浴室与我之间还有一个作为必经之路的卧室。在走向浴室的途中,不仅我的物质身体穿过浴室,而且我的意识也“穿过”了浴室。在“我—走向/意向—浴室”的结构中,卧室并不是悬挂在浴室外部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件,而是内含于这个我与浴室之间 的“走向/意向”这一双重媒介之内的半透明性。我并不能径直地,毫无阻滞和间隔地,直接接触浴室,浴室要成为我的意识对象,而不是潜在的背景,就需要被置于另一个潜在的背景之内。就像透过一块花玻璃观看景物时,一般而言,我的意识仍然穿透过这块玻璃,但同时,我的意识随时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阻滞于此,从而可能顺带地注意到,或完全被吸引向玻璃上的花纹。而施耐德恰恰只能毫无保留地穿过媒介,他没有在媒介中停滞下来的能力,当他不是作为目的地而只是路过某个场所时,他将完全认不出这个场所的意义,除非他重头再做准备运动,把它变成新的目的地来理解。施耐德的媒介只有通行或打断,而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阻滞或模棱两可的半透明性。
这种由于媒介的厚度而展开的世界形成一种意义系统,这个回旋空间越是大,意义就越是丰富。例如书写的目的在于传达语词,但在达成目的的途中却难免要“拖泥带水”,书写和阅读过程中我们并不总是毫无保留地精确地呈现语词本身,而总是要在纸面上滞留。而这种滞留在汉字中更加拖泥带水,更具有多样性,因此在中国可能形成如此丰富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的意义空间既不在于作为载体物的纸和墨本身之中,也不在于通过载体而指向的语词本身之中,而正是在于通过纸墨呈现语词这一活动,这一个作为“通过”的居间的回旋空间之内。而一旦这个媒介的厚度被压平,一旦我们在对象面前失去了“退路”,就将造成施耐德的障碍,——“意识的本质就是向自己准备(提供)一个或多个世界,也就是说,使自己的思想作为各种事物出现在自己前面。意识通过不可分割地既呈现而又舍弃着这些景象,证明着它的活力。世界结构——沉降和生发的舞台——处在意识的中心,正是通过这种‘世界’的拉平,我们才最终能够同时理解施耐德的理智障碍、知觉障碍和运动障碍……”115,152施耐德的“舞台”变成了一块单调的平地,舞台上不再有随时可能分散观者对于表演者的注意力的丰富的布景,观者在表演者面前变得毫无退路,要么只能盯着它看,要么只能换另一个演员上场,场景本身不再具有阴影和多样性。于是,施耐德也变得缺乏“趣味”,缺乏自由,他不会游戏/演戏(play-act)——“就是暂时置身于想象的情境,就是通过变换‘环境/媒介(milieu)’来寻找乐趣”119,,157
施耐德病例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在他的意识世界中,“媒介”几乎完全失去了厚度,变得完全扁平化。但这并不是疾病的唯一形态,在一些较轻的病例中,媒介的缺损将以各种具体的状态呈现,例如梅洛庞蒂提到的“数字盲”,他们可以利用数字来对着实际的对象数数,但无法脱离实际的对象来构想抽象的数字的意义。“媒介的厚度”能够解释诸如此类的各种病态或障碍的情形,但又不至于取消它们的多样性。关键在于,所谓的“媒介”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玄学概念,而是每个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身体,包括他的肉体,以及他的经历、经验和训练,包括它的延伸(工具、技术、环境)。所有这些“物质”的东西同时也是“意识”的组成环节。
最后附上一些辅助理解的图式:
日常行为(具体运动):意识→→身体→→对象
——在日常行动或者具体运动时的意识是直接穿过身体(媒介)的,类似于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上手状态中,媒介从未完全退隐掉,并未完全透明,而总是带有某种阻滞的。例如拿锤子砸钉子时,即便我的意识穿过了锤子完全聚焦在钉子或待修理的器物之上,锤子的存在也从未从我的世界中完全消失。锤子呈现为我操作钉子时的某种阻滞,它沉重、生硬,我必须费力地挥舞才能够砸进钉子。当我砸的越顺手时,锤子就越是隐匿自己,但它始终都潜伏在我的意向活动之内,这就是为什么一旦钉子没砸好时我能够立刻来调整握锤的姿势(或者一个人可以在试图看清对象时下意识地扶一扶自己的眼镜,可以一边看着远方的景象一边调整望远镜),我能够随时把钉子悬置起来,朝空中挥舞来掂量和演习。有时候我也可以一边不停地捶打着钉子,一边掂量调整握锤的姿势……这些意向的切换或游移往往发生于同一个行为过程之中。一种媒介物除了呈现对象或作为对象呈现之外,更基本的状态是作为媒介本身而在意向空间中存在,这种存在并不是作为意向的对象而显现,而是在意向过程中若隐若现地浮现着。整个意向之流就是这样一种有厚度的回旋空间,在一种客观化的反省下,我们把意向之流的其中一个端点认作“主体”或“意识”,而把另一个端点认作“对象”,但这两个端点并不是现成摆好的(然后再在两点之间找出一条连线),而正是在这条并非线性的连线中构成的。
机械论科学(身体自在): 意识→→【身体】
——机械论科学把身体完全当作自然物来研究,就好比摘下眼镜来客观地观察眼镜,在这个时候你往往需要换一种观看方式或换一副眼镜,而不再延续原来用那把眼镜时的行为。机械论科学的反思中,身体已经不再作为媒介了,但它当然也无法“直接”和身体打交道,而是有意无意地引入了新的媒介,例如科学的概念、实验数据等等。机械科学的研究在根本上的困难是难以提供真正的“理解”。
理智主义心理学(意识自为) 意识→→【意识】
——理智主义心理学的问题是过于抽象,过早地撇开了现实的对象而急于进入意识的领域。但没有注意到事实上所谓的“意识”领域无非是展开了的意向空间中的一个端点,而如果撇开了整个意向活动,那么这个端点也就无所着落,只能成为一个抽象的虚设了。
现象学反思(抽象运动): 意识→→身体↔↔(对象)
——现象学反思并不是某种与自然状态完全相反的东西,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自然状态与反思状态也经常互相切换。它们都是指向对象的意向活动,也都是通过媒介的意向活动,这一意向活动也总是有厚度的“回旋空间”,只是在自然状态中,媒介处于隐匿或透明的状态,而在反思中,我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象虚化(加括号),或者干脆虚设一个对象。
施耐德病态的具体运动: 意识→→身体→→对象
——由于媒介的扁平化,回旋空间被极大压缩,意识在对象面前“无路可退”。因此施耐德不仅不会抽象运动,他的具体运动事实上也与普通人不同,失去了模糊性和暧昧性,失去了“自由”。
施耐德的病态的反思行为:
意识→→【对象1】
意识→→【对象2】
意识→→【对象1对象2之关系】
——施耐德只能作对象性的反思(或者说复述),他难以体会媒介作为媒介的存在,而只能把媒介性当作某种客观的“关系”来指认。
施耐德之所以不能理解类比(如皮毛之于猫如同羽毛之于鸟):
正常人:
施耐德:
施耐德勉强地分析:
游戏/演戏(施耐德不会游戏): 意识→→【媒介】→→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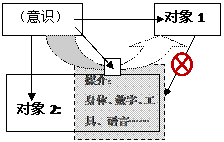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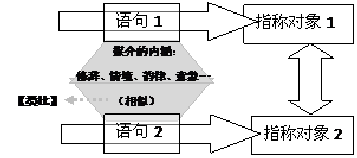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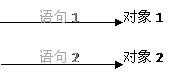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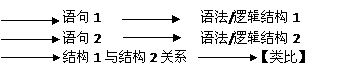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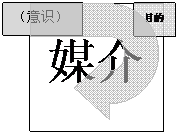
红色部分为今天增补
Pingback: 随轩 » 为什么说诺基亚会成为下一个柯达
Pingback: 随轩 » 西昌会议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