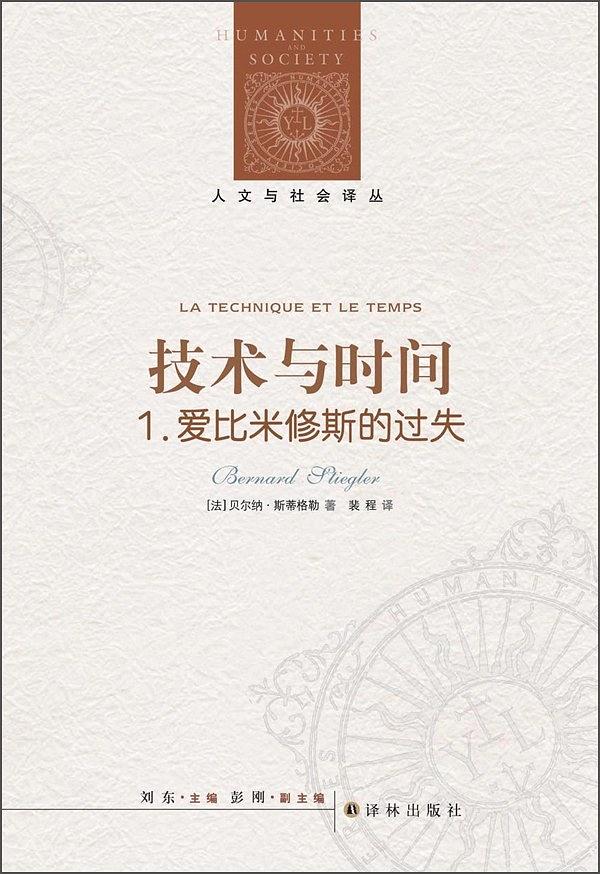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书城》杂志2020年4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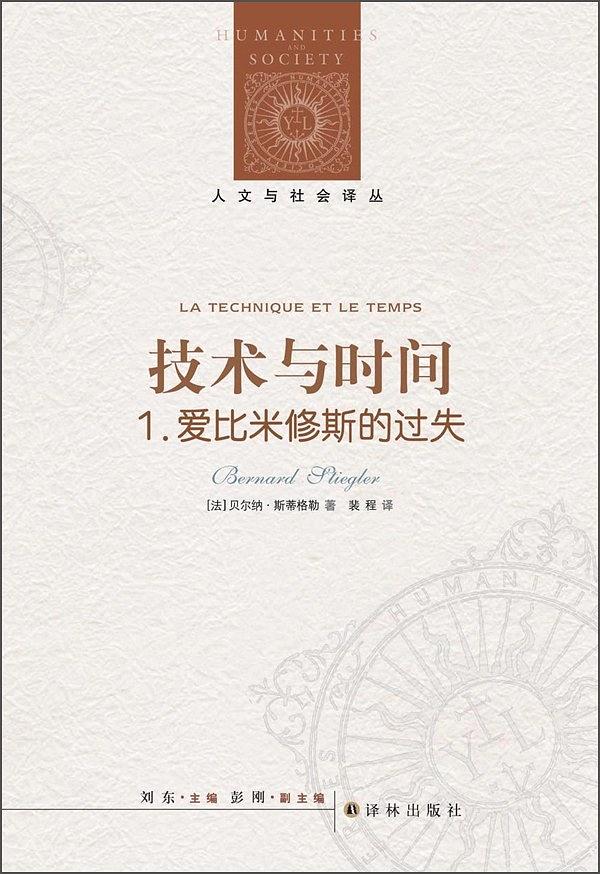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在技术哲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他本人也经常来中国举办讲座、开设课程。他2016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课程讲义最近刚刚结集出版(《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辨证法》》)。而他早年的成名作,《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中译本,在断货多年之后终于也出了新的版本。
《技术与时间》脱胎于斯蒂格勒在德里达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他也的确深得其恩师真传,文风深刻而晦涩,阅读和翻译都并不容易,相对而言,第3部的中译似乎更加讲究一些,而第1部的中译相对而言问题更多。好在这次的新版本略有修订,把“上手—现成在手”这一对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修正过来了。在早前的译本,译者和中文学界的惯常译法恰好相反,把通常所说的“上手“译成了“现成在手”而把“在手”译成了“手下”,读起来非常别扭。
但新译本的修订是很有限的,个别地方改得很生硬或者还没改过来(如第207页:“……人类不再具有任何在手的现成物”应该是说“……不再具有任何上到手头之物”)。另外一些术语和人名也没有沿用学界通用的名称。
不过我不想对译者有过多苛责,事实上,能够基本流畅可读地翻译完这样一部艰涩的著作,是很了不起的。有些术语虽然没有沿用学界定译,但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事实上,斯蒂格勒本人在阐发海德格尔“上手—在手”概念的时候,也并不严格遵循海德格尔的本义,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挪为己用了。非得坚持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解读这些概念,或许反而会阻碍我们理解斯蒂格勒的思路。
海德格尔是在人操持烦忙的语境下谈论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的,在顺手拿起锤子捶钉子的时候,锤子是“上手”的,好像身体的一部分。斯蒂格勒那里,“上手”同样也是指这种把技术器物看作身体一部分的状态,但他更多是从技术史或人类史的语境上说的。在斯蒂格勒那里,某种原始的“上手状态”是一种神话构造,是一种对人的起源的理想化,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原始人”因为“一切上到手头”,“集一切于自身”,所以“不缺乏任何东西”、“不依靠外在世界”(125页)。而一旦开始了“外在化”,一旦开始向自身之外寻求“现成之物”,这就是人类或技术的起源。
在斯蒂格勒的意义上,把“上到手头”理解为“现成”倒也有一定道理。海德格尔那里,“现成性”指的是某种“与“如臂使指”、“得心应手”相对立的“外部性”。上手之物被活用为身体的一部分;而现成之物显得更死板、固定、客观地摆在人的外部。但在斯蒂格勒那里,恰恰是“持留于外部”的事物才“活”了起来,死亡与时间性在这种“遗失”中被开启出来。而“一切都上到手头”的“原始人”还不是真正的活人(有死者),他们没有缺失,没有遗忘,也就没有“时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上到手头之物恰恰更具有“现成性”,而在手之物或者说“遗失在外”的事物,恰恰并不“现成固定”,而是有某种自我推动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动力——“技术逻辑”或“技术趋势”。
译者能够遵循学界主流,把这些术语修订为学界通用译法,当然是件好事,这更方便我们注意到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等哲学传统的承继关系。但是,我认为也不必把“术语”们太当回事。海德格尔本身就是喜欢用文字游戏的方式创造性地使用各种俗语,他本人把语词看作“指引”或“路标”,术语的意义是提供某种引导,指引读者从日常思维中逐渐超拔出来,走向某一条沉思的路径。但一旦深入走下去,每个人会遭遇到自己的道路,而不再应该驻留于某一块路标之下停步不前。如果一块路标下围绕着许多人指指点点、流连不去,很可能说明这块路标并不是一块好路标。
许多哲学工作者皓首穷经,做的事情往往是把哲学家们设立的“路标”从思想之路上拆下来,放在标本室中反复赏玩、显摆。他们试图把术语的意思固定下来,由自己霸占权威的、专业的解释权,最爱指责别人误用、滥用、错译……这种做法至少在针对以现象学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传统时,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这是以一种反现象学的方式研究现象学。
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晦涩的哲学著作?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参与某项“比赛”,比拼我们谁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到作者的“原意”,那么我们确实需要字斟句酌务求精准。然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借助这些思想家,启发和引导自己的思维,让我们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或更深刻的洞察力,最终还是要来回应我们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或许不该过多苛求精准。
斯蒂格勒和德里达一样,喜欢旁征博引,借用各路名家的概念,但细究起来,他的引用经常也未必准确。关键在于,他的论文并不是旨在解读海德格尔或解读柏拉图之类,他的文章要解读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技术时代”的问题。
所以说,虽然这部书晦涩难读,但也未必需要读者一定要预先了解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之类,不需要非得是一位资深的哲学专业研究者,才能来阅读这本书。任何对技术时代和人类命运有所关切的人,都可能从这本书中获得启发,
斯蒂格勒在近几年更多地使用“人类纪”这个概念,而在《技术与时间I》中他还未注意到这个概念,他更多以“技术时代”来指称这个类似的历史境遇——“在当今的技术时代,技术的力量具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95页)。
斯蒂格勒讨论的起点,就是这种时代性的普遍关切。无论在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看来,技术的力量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随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于是,这种强大的力量究竟能否得到合理的“限制”,就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当代技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弄清楚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和引导技术的进化——即技术的力量”(23页)。
对这种时代处境有所忧虑的,当然大有人在,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底色。“虽然抵制技术自古就有,但这个现象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常见问题”(42页)。家庭主妇们都会抵制“技术”,追求所谓“纯天然”的食物、化妆品或生活规律。
像基因编辑这样的技术发展更是引起了普遍的警惕。斯蒂格勒当时就提到了这一方面——“遗传学的操纵……影响到人类‘最自然’的实体和本性。”(94)
上到顶尖实验室和国际政治舞台,下到普通家庭的厨房,无时无刻都在上演着激烈的“技术与自然”之争。
但斯蒂格勒并不停留于忧虑之中,也并不是简单地希望“弘扬人文、抵制技术”,更没有简单地“站队”某一边。他思考的是,当我们谈论技术和谈论自然时,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基因编辑或许背离了人类的本性,或许没有,但是关键在于,斯蒂格勒问道:“什么是本性?”
他注意到,技术时代的独特境况,已然“从根本上触及了‘什么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类问题本身的提问方式”(94)。
斯蒂格勒就是这样出发,从技术时代最流行的关切出发,
那么这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这一点普通人也都能说出一二:无非就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斯蒂格勒也提到“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它的进化速度。” (25页)但这一简单的结论中也蕴含着深刻的问题,首先,什么是“速度”?速度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将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组合起来考察。” (25页)
以及,我们谈论的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空间)的速度呢?我们说刘翔速度快,那是指他在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得快,但他游泳的速度未必快,吃饭的速度也未必快。谈论“速度”,总是要有某种尺度,某种“轨道”来作为参照的。那么,当我们说“技术进化的速度快”时,它的“跑道”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谈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呢?刘翔是一个人,炮弹是一个球,它们都是边界分明的个体,但“技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它的边界在哪里呢?它以何种样貌运动呢?
斯蒂格勒借用了西蒙栋等人的思想,引入了“技术体系”、“技术趋势”等概念,来理解“技术飞快发展”究竟是指“什么—在哪里—朝何方”运动。而“时间“问题是最为复杂的,斯蒂格勒最终要揭示出“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中,不如说它构造时间”(30页)。
总之,“现代技术飞速发展”这样一条寻常的说法背后,蕴含着关于“自然”、“人性”、“时间”、“空间”和“存在”等等基本哲学观念的大问题。斯蒂格勒从技术时代的普遍关切出发,很快进入了哲学史中最深刻、最复杂的问题之中。
斯蒂格勒对哲学史的援引是六经注我式的,他并没有陷入哲学术语的细节辨析之中,他最主要的论述风格,是对古希腊神话的重新阐释。正如《技术与时间I》副标题“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所提示的,围绕着这一神话隐喻展开的讨论是这本书的主题。
这种隐喻式的文风当然不容易理解,但斯蒂格勒动用神话寓言,恰恰是要破解关于人性的某种根深蒂固的神话。
斯蒂格勒认为,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技术中心论,无论是认为人性控制技术还是技术控制人性,都预设了某种作为“自然”(nature/本性)的固定的、作为普遍原则的东西,而斯蒂格勒认为这种人类学家设定的“人类本性”是可疑的——“我们不再像人类学那样假设人类有一个固定的本性(或起源)”(100页)。
这种固定的人性观以卢梭为代表,卢梭在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构造了一种“完美的原始人”,他认为科学、艺术或技术都是在某种基本的、纯洁的、质朴的自然人性之上“外加”的东西,这些“外加”的东西导致了“不平等”,而人从本性而言是平等的。诸如洛克、霍布斯等等,虽然具体观念与卢梭多有分歧,但也以各自的方式设定了某种作为普遍原则的理想人性。他们的思想至今还深刻影响着今日的政治话语。
这就是一种“现代的神话”,这类神话奠定了我们时代中“自然”与“技术”的根本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者和技术至上者是一致的,区别无非是前者希望在“自然——人——技术”这一谱系中,人应该向自然这一端靠拢,而后者认为人应该向技术这一端靠拢。
这一神话并不是科学的结论,基因学和古人类学也许可以追溯出猿人何时开始直立行走,但并不会告诉我们“人性”是什么。相反,在许多科普文本中,渗透着许多“神话故事”,如所谓“解放双手”、“改造自然”等等。人与动物的差异,人与自然的对立,往往被当作某种确定无疑的状态。
相比于潜移默化地支配着整个现代性的“人类学神话”,斯蒂格勒对希腊神话动用,就显得理直气壮了。所谓以药解药,以毒攻毒,斯蒂格勒在这里试图以神话破解神话。
人类这一物种当然是独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有某种固定的本性,如果说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有某种独特之处,不如说这种独特之处在于“欠缺”,在于“无本性”。斯蒂格勒用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寓言,讲解了这一独特之处——其它动物有的有尖牙有的有利爪,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先天就确定了的“器官”。但唯独人类,天生是孱弱和匮乏的,仅仅依靠先天的器官并没有生存的能力,因此必须通过后天的器官来延续生命。这种后天的器官,即技术器物,被斯蒂格勒命名为“代具”(或译“义肢”)。
在这一视野下,技术器物就是人的“外在器官”,斯蒂格勒重新阐发了“器官”一词,认为它同时“表示肌体的有部分或作为技术器械的器具”(50页)这种把技术作为“有机化的无机物”来分析的视角,早已被马克思开辟出来。推进着马克思的思想,斯蒂格勒把人类史和技术史放在一起考察。
这种外在器官与生物体内的器官大不相同,这些器官不止能够“得心应手”,也能够现成地“遗留在手下”,被“放下”的器具又可以被“拿回来”,借助外在化,人类可以遗忘和回忆。一个生物的内部器官随着它的消亡而消散,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再多后天的努力都无法把动物针对内在器官的改造传递给后代。但是外在器官则不同,它们和DNA一样,也是某种“遗传物质”,可以被前人“放下”而被后人“拾起”,代代相传。而这些“遗传物”也和DNA一样,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人类与一般生物大不相同,他同时具有两种尺度上的“遗传”,因此也就有两条维度中的进化史。斯蒂格勒用“后种系生成”一词命名这一进化维度,或者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叫做“后物种起源”。
斯蒂格勒通过重新讲述“人类起源”的神话,把人的自然(人性)和人的造物(技术)在源始的意义上联系起来。“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与客体。”(148页)
“我们制造了工具,工具反过来塑造了我们”这句格言来自丘吉尔,被麦克卢汉发扬光大,这一洞见本身也不算特别。但斯蒂格勒的贡献是,把“技术形塑人类”这一朴素的观点,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背景下考察。他紧接着说道:“这个假设彻底推翻了柏拉图以来……关于技术的传统观念。”(148页)
斯蒂格勒推翻的不只是柏拉图以来的技术观,事实上被推翻是柏拉图以来的“知识观”。
前面说到技术器具可以被遗留在外并重新“拾起”,但技术并不是人天生就会的能力,而是需要“学习”。但学习是何以可能的呢?
斯蒂格勒认为这一问题起源于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呈现的诘难,“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这本身就是哲学史一切思想,尤其是现代思想的动力”。但柏拉图以来,这一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斯蒂格勒从技术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这一哲学史中最核心的问题(这部分内容更多体现在《技术与时间3》中)。
当然,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未必要深入哲学史的细节,追随斯蒂格勒与柏拉图、康德、胡塞尔他们展开争执。但所谓学其上得其中,即便我们对许多晦涩之处不求甚解,也能够在阅读中得到启发和冲击,引导我们在这个技术时代重新思考“人是什么”。